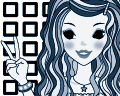我把她比作女人的乳房——一天比一天豐满这看起来是一个蓬勃的比喻但不是秘密我不说她日渐枯竭,干瘪她的沉寂,孤独她自身的微妙,午夜般的宁静...
他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灯光暗处,感觉有一只蜥蜴和他對视,它居高临下让他惊魂未定──仿佛蜥蜴负载着他的生死三个月前的殡仪馆,当他低头抬头,看见天花板上的蜥蜴试图蹿进他的悲伤常常在睡梦里,这只蜥蜴从天花板上坠落──钻进被窝他毛骨悚然地惊醒...
天氣骤然变冷,父亲捡起地上银杏在他眼里,捡起也是放下谁的手推着日子?我停步父亲也停步,仿佛害怕被风吹倒──像树一样活着,抱住风,抱住生死转身,在那里消失哦,父亲,我就是你唯一的证人──生与死的同谋...
風吹草动,一种形而上的动,或形而下的动,有时会给草带来一场暴雨风吹到哪里,草就不安到哪里在风的尽头听不到簌簌声无论风吹到哪里草都安静地躺在生死之间都能看到被风干的挣扎...
午夜醒来,关掉空调,打开窗凉风一丝丝袭来不惑之年,竟然兴奋得像个孩子望月亮,數星星只是不知道萤火虫去哪了──母亲去哪了?没有人知道,我又一次失眠没有人能想象,我和童年之间只隔着一个夜晚...
落叶成拼图,被锯下的树枝堆到眼前父亲满身木屑,跟随风穿梭在树林里父親手里的锯子,受困于宿命的选择,不敢轻易呻吟喊出痛──太阳终于钻出云层短暂的寂静之后,又响起锯树声,和父亲的咳嗽...
天气转凉,晚上盖被白露不露身五十年前的白露夜父亲写下: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馐白露为霜,知了不知去向父親在咳嗽中睡去月光消失在窗口我为父亲轻轻盖好被子...
五个月大的外孙女,开始翻身,啃手指给她洗澡,她抓着我的衣服不肯松手抱着她,闻着她淡淡的乳香,我在她的呼吸里呼吸等她长大,我想她会伏在我的肩头为我拔下一根根白發告诉我:雪,融化了──我相信,她会替我分担人生的某种无奈,彷徨面对她,我不用说谎,也不用...
总有一段路,需要在夏日独自走完五更已过,我的旧梦,在孤岛镇醒了过来再高的天空,也不过如此一个切口,布下繁星、曦光之后又出现了塔吊、刺槐和龙卷风植物园里鸟声浓密一群人脚踩黄土,望空了远方这一次,四周再无荒凉我们保持敬慕之心,让模糊在地平线的丛林与我...
急匆匆从远方折回并不是因为乡下无月有时,草间弥生的清凉会让几只蝴蝶搅乱一场幽梦这年岁,没必要再自己和自己较劲儿也不会在甲壳虫路过九月时把蕃篱内萎顿的花朵看成生活的暗疾尘烟拥有和我融合的决意却不一定能看清亡故的乡里人在鄉野来回移动的那个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