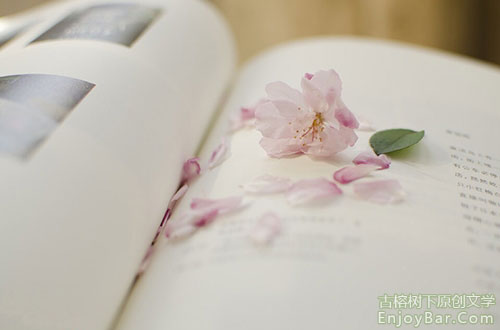“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清明节的千古绝唱了。自古以来,人们都在农历的前三后四这一个星期之内去野外踏青,扫墓,祭奠亡灵。其重视程度,几不亚于春节,特别是在农村,全家老少男女,带上祭品,镰刀,锄头络绎不绝于野。修坟,割草压纸钱,焚香叩头,燃放鞭炮,寄托着人们对故去者的思念,乞求着亡灵对生者的祝福,希求着阴阳两界的勾通交流,表达着人们缅怀过去,希冀未来的一腔热情。
今年的清明节前天气晴和,阳光明媚,回乡扫墓的人异常的多,辆辆班车都挤得满满的,只要车一进站,人就涌进车厢,我和妻子好容易才抢到了座位。
“绿遍山原白满意川,子规声里雨如烟。”清明这一日的清晨下起了阵雨,烟雾缭绕,雨水在山原绿草中流淌,漫山遍野,绿草青葱,鸟儿啁啾,盎然春意阵阵袭人。回到外家,老外公带着子孙十多号人浩浩荡荡地去扫墓。这乡下的野外,处处是人群,一家一家的都穿红挂绿,携妇将雏穿行于荒郊野外,有汽车的开汽车,有马车的驾马车,但不管坐什么车,当多大的官,车到山前他还得下来走路,还是得给故去的先人磕头,这也叫众生平等吧?
牛在草地上优闲地吃着青草,小溪欢快地流淌,象原野上奔跑着的儿童。老人们沉思庄重,儿孙们兴高采烈,这泥泞的道路阻挡不住鲜活生命的掀泄。公路边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在这永福堡里的深山中是不易见到,但花开红树乱莺啼的景色倒随处可见。爬上山坡,欢腾的小溪哗啦啦地奔腾跳跃,树木杂在蒿草中青翠欲滴,好容易爬到了祖先的坟前,年轻的挥镰割草,锄地培土修坟,小孩子们耳听着长辈讲这是你祖爷爷的叔叔,或是爷爷的爷爷的坟,讲那个时节老辈人怎样风光,可孩子们的心却早在掂记着茶子树上的茶片哪一片好吃,掂记着篮子里的鞭炮什么时候好点。摆好香案供品,在坟上压冥币纸钱,老老少少叩头乞福,再烧一堆纸钱供老祖宗在地府中风流快活,话都没说完,小子们迫不及待地点起了鞭炮。
据岳母说,土葬是很费人力物力的。人还没有死,就早早地看好墓穴,请风水先生或自己看都行,然后找山的主人谈价买地。死后祭奠操办白喜事时,还要请吹鼓手还要唱道场,超度亡灵择日上山。如果那一段时间日子都不好,就要在家中一直停放到良晨吉日,天气一热,电风扇加冰块齐上阵都压不住腐烂臭气的侵袭。埋下去几年后估摸着肉化骨枯,还要去捡骨头。捡骨头也很讲究,请专人去捡,挖开坟墓,打开棺盖,斯人衣物如旧,仅露面部森森白骨:两眼窝深陷,鼻洞朝天,白牙寒灿,没有经验的人会禁不住背冒冷汗,环顾欲奔。只见捡骨人口含一口酒“扑”的喷向棺内,然后用手伸进棺内一扯故人的裤管,裤管哑然应手而碎,露出腿筒骨一根根,脚趾骨一节节,然后捡骨人从脚趾骨开始捡起,从下到上逐一放入“金坛”中,就如同请先人座在瓮中一样,这使得我想起了桂林甑皮岩人的屈肢蹲葬来。远在一万年左右的桂林甑皮岩人就认为人在母亲肚子里时是团身屈肢的,所以死后也应屈肢蹲着回去,他们把死当成回去,“视死如归”,很有道理。捡骨时,若骨质黄爽得好,就把装骨头的金坛埋在原来的坟内,若骨质发黑还起了青苔,就说明此坟地不好,应择日改葬他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子孙多灾多难,骨质好也要改葬;若人旺财茂,骨质不好也不必改葬,不过还是要稍微改善一下坟墓的小环境,如挖排水沟,使坟墓干爽。迁坟也是一件大事,宗族的人要同意,长辈要在场,碑上刻那些人的名字都有讲究,还要祭祀,择日等等。听岳母娘讲清明节的事,我心里沉甸甸的,我们这艰难困苦的人民对祖先的崇拜直如一座大山压在肩上,这份精神寄托又何尝不是一份重负?
云雾越来越浓厚,路越走越泥泞,春的欢欣变成了劳累饥饿的难行之路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杜牧要把清明时节行路人的神态写成“欲断魂”了:沉重的追思,沉沉的雾气,泥泞的道路,几如丧葬的悲呛,能不让人“欲断魂”吗?杜牧笔锋再一转:“借问酒家何处有?”歇歇疲乏的身心,毕竟是清明,春意挡不住:“牧童遥指杏花村。”还是一派生机盎然繁花似锦。
回去了,在回桂林的车上,同车的几个乘客聊天聊起清明会来了,他们讲着讲着,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满脸兴奋得通红,那清明节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所谓清明会,就是家族中有身望的老人在清明节时召集全族人聚会,先祭祀祖先,后念族训,众人一心,同心协力,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一致对外,然后大吃大喝一顿,修坟修祠堂认定同族,从今往后,不管天南地北,只要讲出祖宗,背出族训,就是一家人,就要无条件互助等等。听着他们讲,我脑海里浮现的不是现代文明而是远古洪荒时人们苦苦的挣扎,是宗族间的械斗。“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多美的春天啊,可天空中那飘飘摆摆的纸鸢带着的是人们怎样的愿望和希冀呢?望着膝上的儿子,望着“雨如烟”的原野,在汽车马达声中,我深思着,一晃而过的坟头上纸钱纷飞,片片山原上杜鹃花火红,我不禁脱口吟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清明扫墓的感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