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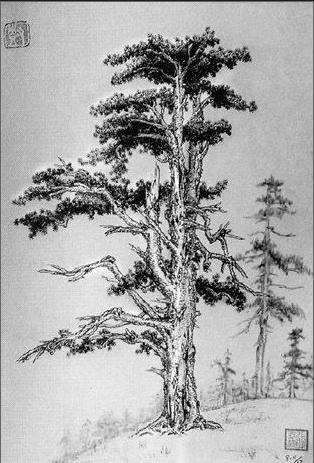
在评审首届萧红文学奖时偶遇叶弥的小说,欢喜中便找读她的系列作品,我发现她的小说有别样的气质和高妙的品质,实在高出不少当红女作家,尤其她的短篇小说。她擅长书写游走在日常伦理边界,有着一根筋决绝性格的普通人,书写他们与现实的尖锐冲突并见证人性的复杂。这些坚硬如水的人物背后,是一种时代无法克服的社会性伤痛。叙述沉静款款,故事内核尖锐,小说气质却俊逸独特。于是,我便在多次会议呼吁“叶弥是位被低估了的作家”,“读叶弥,有背对月光,却光影清凉,一地忧伤之感,并难以释怀”。近日读到她的《亲人》,认为其是她《成长如蜕》后又一出色之作。
如果说《成长如蜕》以父与子为视角;《亲人》(《作家》2013、1)说的则是母与女的故事。私生女何湘在16岁时,实在忍受不了母亲强迫她每天到亲生父亲家吃晚饭的屈辱,终于在她父亲一家也无法忍受如此尴尬而蒸发后的大年夜,一声不吭地离家出走了,并与母亲失联8年。一天,在街上偶遇人们围观一位坐地哭喊妈妈的女孩,触景生情:“何湘到了家,把车子停到车库,熄火,关门,背了包进门。脱鞋时一低头,脸上掉下一滴水珠,沉甸甸的,里面像是包含着什么惊人的元素。一摸,竟是一手的眼泪。何湘想,哦,我是有妈妈的,只是八年不曾相见了。”于是,何湘走向寻母之旅。寻亲之前及过程,矛盾百出,内里紧张,作者沉静款款地展示了何湘无爱的伤疤,一种拒绝亲情、爱情与友情的冷漠孤独的人生;旅程之后,尤其与小二的偶然一夜情,以及寺院老尼的出现,矛盾平息,伤疤愈合,何湘坚硬冰冷的内心一步步回暖,温暖到心底最柔软之处,此时她也找回了爱的能力。“可不是,世界就是一张纸,轻轻一捅就破了。在破裂的地方她看到了真相,这真相就是爱。”而人人都有可能寻找到亲人,因为“爱,就是找一个亲人,性,也是为了找一个亲人”。在别人的眼光里,何湘找到与出家了的母亲兰坚和解的钥匙,自然也找到了直面这个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找回了自我。老尼女人说,兰坚和我说过的,你就是为了在老陈家里吃了六年晚饭,才记恨她。你不想想,老陈一家子,让你吃了六年晚饭啊,你是多大的福气啊?她忽然惊诧,可以这么想的?原来小二的思维与这女人是一样的,世上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一种思维不断地得到,一种思维不停地失去。“我一直以为伤害我最深的是我妈,因为她,我体会不到爱。”
八个月后,她被推入产房,什么都好,护士对她柔声曼语,医生对她抚慰有加,同病房的产妇们给她送了鲜花,她的同事们在产房门外等待她,他们都像她的亲人一样。而她呢,这个单身母亲的嘴角和眼睛里堆满笑容。医生刚才问她,孩子出来以后,她要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孩子呗,谢谢孩子来投胎。
一如长篇小说《成长如蜕》的“弟弟”顺应了时代,顺应了世俗生活,结束流浪,脱壳重生般回到了父亲希望他走的人生道路,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何湘也换了一种角度,人生便有了亲人和爱心。作为读者的我们也与作者叶弥、主人公何湘一道,在历经悲凉之后,抚摸各自的疼痛,也去寻找各自的亲人,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故事简约,内在的节奏感却很强,渐次深入并拓展张力,既凸显其丰富的内核,发人深省,充满宿命感,又内蕴着决绝尖锐的悲凉和慈悲。
而叶弥另一短篇《香炉山》(《收获》2010年2期)也堪称精品,女主人公夜游香炉山,本来是“一个享受愉悦的机会”,却因不久前一桩凶杀案而令她心里充满了对未知旅途的戒备和慌乱,让她不能静下心来欣赏过往的村落。心灵的旅程使她的内心世界不断产生裂变,信任的缺失让她在山脚下迷路,哪怕千辛万苦如愿登上了香炉山,也看不到神灯。苏给她的一路一夜的信任,她与何湘一样心灵回暖,重新找回无所畏惧的自我。这个探寻女性幽微心理的小说,与《亲人》一样都是关乎女性心理和自我救赎的寓言故事。当然,叶弥的叙述是上乘的,她总是把自己安置在静处远处低处。目光细致,文字才沉静。静静的温温的却充满轻盈、灵性和诗意,如飞舞的彩练。感觉如丝如绒,细微如绒毛般质感;却又丝丝抽出,拉长,舞动着飘向远处,简洁又意味绵长;尤其她深谙文学的虚实之道,一如《亲人》结尾车祸时的灵魂出窍,似虚似实,人物对话的双关意蕴,有计白当黑之功用,简约却内核扩大,偶然故事的背后,常常是发人深省的必然。这神来之笔既揭示了故事,令人震动,还使小说因另有细节而富有意义。
其实,表现笔下女性个体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强烈对峙,并在左冲右突后,逐渐与这个社会的和解互动,有了直面生存实际的勇气与生活态度,成为当下女性写作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尽管叶弥的文学写作更为深广,也不独以女性的个体性经验写作为特点,但《亲人》《香炉山》在某种意义上却揭示了当下女性文学这种文学现象的内在根源,女性的自闭并非仅仅是个体的,也是集体无意识的,更是时代的精神症候。无论男女,换一种角度,便可以找到另一种人生和人性光辉,从而直面人生,或回归生活本身。19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在文学上突显女性的性别,以一种女性的独特的个体性经验解构着男权社会,如今历经世事的她们也一如叶弥般解构着过往狭窄自闭的个体性经验,走出个人世界,改变消极的避世态度,并与笔下女性经过命运百转千回而回归正常人生,并实现了治愈性的心灵疗伤与自我拯救。
于是,当下女性写作已经走出一个人的战争了,因为“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女巫林白们已经双脚着地,走进人间。这份与生活的互动与和解,不是败退的妥协,而是更高层面上的直面人生。
林白与海男,都是颇具艺术天性并特立独行的女作家,她们的女性精神困境和苦难的小说系列,持续地提供着对于女性历史与个人的经验思考,作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个人化写作的代表,她们的作品不仅具有先锋意义,而且为读者提供持续而长久的对女性文学的阐析。近年,她们笔下的女性在一个人左冲右突的战争中,开始与生活的周遭有了不同程度的和解互动,感伤、自闭与伤痛的身心,走上了有阳光暖意的治愈性的心灵疗伤与自我拯救之路。林白从《一个人的战争》《玻璃虫》《万物花开》到《妇女闲聊录》《致一九七五》再到《北去来辞》,终于出现了史道良这样一位传统而俊朗的男主人公,一位不同她以往笔下那些漂亮俊友的猥琐、无责任心的男性形象,而是一位催生女主人公海红精神成长成熟的智慧型的男性人物形象。海红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而走出个人时空,在她厘清自身与史道良的相依关系后,也看清了自己的梦想与疑难,可能与局限,回归了生活,也找到了精神故乡,或说是精神回归后的自我救赎。于是,聪慧的林白便有了中年以后明亮温暖的平凡生活,作品也多了幽微的人性裂变和丰富的生活细节,重返日常与自我救赎使林白的创作变得内蕴饱满、深长弥坚。《北去来辞》也一扫林白曾经不食人间烟火的“伤感、矫情、自恋与轻逸的自己”,从容地走进生活,融汇了以往所有个人与创作的经验,与笔下人物表现出她最大程度的和解互动、同情之理解。endprint
而“高原玫瑰”海男,在她的新作短篇小说《背叛》(《滇池》2013·6)也表达了与《北去来辞》一样的对男性“同情的理解”。这个也有着寓言色彩故事,不仅在于深掘了女性婚恋中常见的自我陶醉、遭遇背叛、逃离与报复的女性挣扎,更在于挣扎过程中对男女各自潜伏的“异化”、暗流的人性幽微的发现、理解与反思。刚接受男友订婚戒指的女主人公,却发现男友在与另外女子约会;在自我疗伤的温泉,偶遇每年皆来温泉“寻求孤独”的另一男子,跟踪而来的男子的女友揭开生活的真相,并及时阻断即将的艳遇和暧昧。女主人公豁然开朗:“我明白男人为何要背叛女人了:因为男人渴望孤独时,女人走了上来。”海男已经不止于对男性的拷问,更多地对两性各自的人性幽微、裂变的瞬间精确的描述,并充满女性悲情和自省,显示小说宽度的同时,也因她的笔触探寻到人性更隐秘的深处,并透过现象直抵了世界与人性的本质,揭示了人性的深度。这种冲突后的和解互动,不是与世俗的妥协,而是一种对人性更透切的表现与批判。完成了治愈性的心灵疗伤与自我救赎后,女主人公又可以从容回归到日常生活了。
其实,不能面对生存实际的女性,她的灵魂世界也难以圆满,自我救赎更是妄谈。很多女作家,永远不能处理“后半生”如:萧红,张爱玲,伍尔芙等。
文学天才萧红的文字和感情生活也是一个反差的存在,她短暂一生的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彻骨荒凉,而她文学世界却满心温暖,以及她对文学的执著追求、纯粹的文学精神与孤绝的文学品质,为我们留下一笔文学财富。
她的人生是矛盾与分裂的。一如她的名字“萧”与“红”,灿烂与凋零相生相应。她终生渴望爱与自由,也终生在男权文化中受难与自我放逐。即使在最落魄时,她热烈的心也总是扑向不那么适宜她的爱,甚至在新爱中生旧爱的孩子,命运奇崛,爱与自由总是在她抵达时,又无情地远去。她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她一生所承受的不幸、屈辱和痛苦,一是来自她的“爱人”:与她一样处于进步文化阵营、并一起追赶新文化运动大潮过来的“他们”。一是中国的文化土壤所致,因为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历史震动,已深化到性格的内在分裂,萧红既渴望传统的家园,又追求自由精神,抗争专制,就必然在夹缝中生长。因此,四分五裂的中国女性的灵魂,无力对抗人类的愚昧与铁桶般的男权社会,因而充满悲剧与苦难。“我想飞,但是我同时感受到我会掉下来的。”萧红从女性的个体经验出发,追问女性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作品感人至深的是女性的文化处境及其悲剧命运。心里有痛感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文字。
同是旷世才女,滚滚红尘中的张爱玲生活安逸,却也无法面对生存实际,一个胡兰成便毁灭了她灵动深长的情感世界,也造就了她惨淡的后半生。读着她笔致妖娆而阴冷,气局狭小尖锐,寒意沁骨的文学世界,一种怀旧家庭的人生悲凉,不期而至。而生活惨烈的萧红,笔致却素朴天成,气局宏大奇崛,文学世界温暖深切,纯粹执著,那是一种紧贴大地,关于百姓生与死的大悲凉。当然,她们都无法面对人生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无法完成个人的自我救赎。
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伍尔夫又是另一出人生悲剧,她也在世俗的人间与个人追求中无数次迟疑和冲突,实在无法忍受生存实际,于是,伍尔芙选择了自己的灵魂,最终还是离家远去。她注视着虚空,在某一个黄昏,走向那条叫马塞诸斯的河流,上衣口袋里装满鹅卵石,抱了必死决心,沉入波光潋滟的河流,开始另一个国度继续她精神世界的思索。这是电影《时时刻刻》中妮可演绎伍尔夫对尘世冲突的最后决绝,黛色的晚霞留给我一种知识女性无奈无望的悲凉,至今犹在。
便想起叶弥的《亲人》《香炉山》,如果萧红、张爱玲、伍尔夫们换一个角度看自己的人生,一直是失去的同时,是否也一直得到了什么?也许便可化惨淡人生于日常生活?当然,人间也少了一曲曲文学绝唱。
少了面对生存实际冲突的能力,也容易少了揭示人心及其人类异想的能力,是否就是中国女性文学与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门罗的人生与文学智慧的一个重要差距?也许这也是当下女性写作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因为在当下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进程中,女性和文化都被用来指称现代化的程度,那么,与世界多元文化碰撞最为活跃的全媒时代,女性书写的发展必然受到各种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更深刻的冲击和影响,由此也体现出当下女性书写在某种意义上的独特性。当然,女性因其性别的“宿命”而更加边缘、更加敏感、更加易碎的特殊情境,更渴望获得并展示自身的话语权力,既完成女性的自我救赎,又留下更多的为抗争多重压迫所作的挣扎和努力,为人类发现更多女性命运何以如此?人生何以如此的人生与审美经验。也唯此,文学之路才路漫漫兮。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