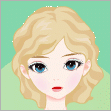延河
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延河》杂志,创刊于20世纪50年代,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光荣历史,在共和共文学的奠基时期有过非凡的表现,号称“小《人民文学》”,在文学火热的20世纪80年代更达到超过13万册的月发行量。她的漫长时期的品牌积累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深刻的历史记忆,至今深入人心。今天30岁以上的中国文化人无疑不知《延河》。新版《延河》将以200个页码的超大容量,立足时代,围绕“文化的文学”、“人文的文学”这一核心理念,把文学放在文化、人文的维度上衡量,重估本时代文学的内在特性,将通过“第
文集访问量: 14305 次
音乐列表
古陶器为何钟情于绳纹而久久不弃呢?我身边这位十三岁的小侄儿,盯着橱窗里的一件陶罐,清澈的眼仁里涌满了狐疑,居然眯成了绳纹状。记得那年去淳化甘泉宫遗址踏青,就发现过堆得如垃圾般的瓦砾,随意用木棍拨捡,偶尔会发现刀刻木划的痕迹,而最多的还是走向整齐的...
怎么也没想到,落满尘埃的岐山博物馆居然陈列着一件小小的“节约”。我的确有点惊讶,急呼同伴过来欣赏,这个被称为“节约”的西周马车零件,是青铜的,就萎缩在那个歪歪扭扭的玻璃橱窗里,静静地注视着突然的造访者。这般小模样,似曾相识的,怎么会是节约呢?老馆...
当我赶到宝鸡博物馆,看到馆长正摆弄被称为“管辖”的古代车辆构件,就忍不住笑了。圆圆的,空心的,小茶杯样的西周青铜件,横插着一个食指粗的销子。这是古时套在马车轴上的构件,但表面布满线条流畅的美丽纹饰,细细看去,竟是许多青铜器上常见图案,前后两个强悍...
下班路过小区,看见摆摊小贩脚下的竹篓里盛满核桃,上面还放着三五个剥掉外壳的,露出饱满的核肉。卖核桃的是个中年人,穿着洗得很干净的旧衣,脸部黝黑,坐在两个竹篓中间,背对小区大门,神色间散散淡淡,像前朝闲民,身旁纸板上写道:核桃,十五元一斤,谢绝议价...
张岱写有《蟹会》一文,我背不下来了,懒得查书,故不引录,有兴趣的自个找《陶庵梦忆》看去。张岱的小品文,起承转合天衣无缝,用的是淡墨,看起来却浓得化不开。读一点张岱文字,能得文章作法。张岱的文法,一言以蔽之:苦心经营的随便。苦心经营容易,随便也简单...
有人不吃花椒,说辣。有人不吃花椒,说麻。我喜欢花椒,做酸菜鱼、水煮牛肉,炸一小把花椒,吃起来满口奇异的香味,吃饭时得多盛一碗,胃口开了。川渝人真能吃花椒。几个人团团坐着,每道菜都放有花椒,青花椒红花椒青红花椒。面条里也沉浮着几颗花椒。川菜在烹调方...
似是一戟惊雷劈入脑海,全体师生肃立。没有人移动,没有人言语,一声声防空警报似是巨鸟哀嚎,低徊盘旋,裹挟着巨大的悲怆与痛苦,时远时近,号叫在每个人耳边。这声音像是一条乌黑的绳索缠住咽喉,又或是一个连绵不休的噩梦要窒住人呼吸。我默立着,垂着头,仲秋的...
在我转过身的那一刻,忽然好似背后传来梵唱,悠远高古,大德之音。苍天博大,降落雨莲花,四面潮涌都似因此一静,有所震慑。嘈嘈切切,温存浪涌。我再一次回眸,打量这座色调温柔的哑白建筑,一浪浪涌来的尽是慈济志工质朴的表白:“我们不知道伟大是什么。”“我们...
六岁以前我住在城墙里,那儿是古都的魂。平层的大院子,讲不完故事的老人,有猫咪抱了尾巴,阳光下睡得安详。那会儿家里是没有电脑的,电视也不甚有人看,头发被妈妈一剪便可上街,衣服发型难辨性别。但想来那时我也不大在意这些,照样天天搬了小板凳乐颠颠地在大院...
有个朋友很瘦,我们喊他山药,有个朋友矮胖,我们喊他洋葱头。很多菜名是绰号,周围还有朋友叫豇豆、扁豆、苦瓜、茄子、西红柿、地瓜。好在没有人叫大米、小麦、面条,若不然可以开餐馆了。我在南方没吃过山药,山楂吃过不少。南方的山楂果肉薄,入嘴酸涩,远不如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