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平
徐水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
第54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开幕的6月4日之前,预展便开放了。《新闻观察网》6月1日的“The Day’s Best”(当日最佳)是中国馆的作品《扩散》的现场图片。图片像中国南方清晨的逆光摄影作品,图中的人物依稀可辨创作者原弓(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读博士)剪影。《东西网站》将另一张原弓在他的作品《扩散》前摆出“大”字造型的图片评为“过去24小时最受外媒关注的中国新闻”。不能说这幅作品征服了西方观众、艺术界和媒体,因为作品的诗意不具备“征服”的天性。这幅作品,正如中国馆的策展人彭峰对所有五位艺术家作品的概括:不是为中国观众创作的,专为西方观众、专为威尼斯设计的。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样的景象我们似乎司空见惯,如同呼吸一样。但本文化之外的观者,有一种异邦的想像。何况在“light”、“vision”(光、影)的西方主流艺术面前,煞费苦心的中国艺术家们没有“班门弄斧”,而是不虑而得地选择了“味”,与本届双年展的主题“IllUMInations”(光明)保持“和而不同”的关系。品味中国馆的作品,用“遇”与“言”两个字似乎最能准确地表述。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中西文化不言而喻的差异性,而是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艺术邂逅在交叉点上产生的效应。
一、光与味的相遇
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IllUMInations”,在意大利语中有着三层含义:照明、灵感与感悟、宗教意义上的启示和启迪。这个词汇的多层含义可以概括为从“从光的照耀”到“神的启示”、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一个语义序列。此主题强调了“光”作为理性象征的古希腊和基督教文明。神的灵光开启了欧洲人的心智,“日神精神”成为西方近代文明的主体。欧洲人对辐射和穿透的“光”也情有独钟,主题“IllUMInations”似乎还对古典社会流连忘返。现代艺术惯于使用隐喻,用游离于两种意象之间的语义来解构确定的认知。“IllUMInations”也具有后现代的意味:在以光影为造型手段的西方艺术和以数理逻辑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智慧之间预留了徘徊的通道,一个确定的词义被本届双年展策划人百思·库莱格(Bice Curiger)肢解,变得无法确定。同时,这种不确定性像皇帝的新装,勾起了观者自我检验认知能力的巨大兴趣。光影?灵感?启示?还是西方理性的光芒普照全球?无法否认的是,主题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是浓艳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使人类分有了神的智慧。上帝创造宇宙时,说“要有光”,“便有了光”。中世纪的哥特教堂彩色玻璃窗让人间分有最高的智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乔托开创了“光”与“影”的艺术。梵高闪烁着法国南部地区的麦田金色光芒的作品等等,贯穿了光的主线。诚然,光的寓意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太阳的光芒也不独青睐欧罗巴。没有光,东西方文明同归于寂。但没有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没有18世纪理性的启蒙,麦哲仑不能环游世界,哥伦布不能发现新的大陆,欧洲的文明之光不能辐射到全球。不可否认光是西方文明的象征,“IllUMInations”的诡异之处在于,世界到处都有光。所以大写的词根“IllUMI”(照亮)后面跟着的是“nations”(“国家”一词的复数)。
威尼斯双年展被称作现代艺术的“奥林匹克”,因为它是世界三大双年展中,唯一设立国家馆的展览。美国馆的面积是中国馆的30倍,意大利国家馆也是一个军械库,但面积有1800平米,且没有老储油罐。由于各种原因,多年来中国馆一直使用这个位于展区尽头的军械库,很多游客因为体力不支而无法到达。中国展馆是一个约200平方米的旧军械库和绿地“处女花园”的一部分。军械库不大的面积还放满了大个儿的储油罐,只留下一个过道可以布置作品。空间是“光影”造型的重要前提,艺术家如何在油罐的夹缝之间生出“莲花”?
中国馆的五位艺术家潘公凯、杨茂源、蔡志松、梁远苇、原弓用各自的方式生出了莲花。潘公凯的《融》制作了-5℃、带有荷香的超大型水墨画走廊。杨茂源的《器》则在很多小瓷瓶中置入风油精,观众可以带走一瓶。蔡志松的作品《浮云》是用牡丹花瓣贴面的巨大云朵,云朵中间包裹着上好的绿茶——杭州狮峰龙井。梁远苇的作品《我请求:雨》不断散发着中国白酒的气味。原弓的作品《空香6000立方米大于6000平方米》用加湿器制造出燃香的效果。在“处女花园”,原弓加湿器产生的水汽飘荡在草地上,于是有了前文提到的“The Day’s Best”现场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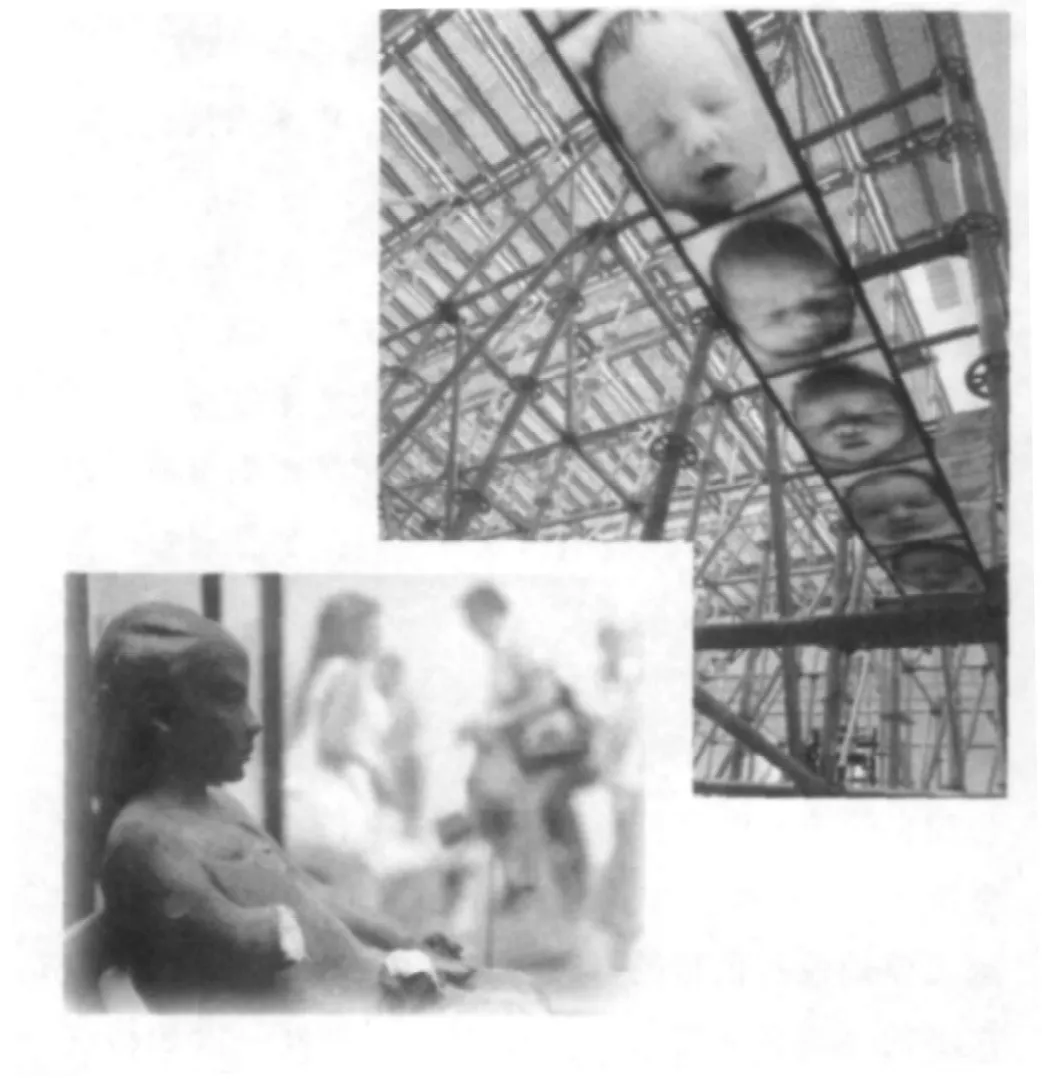
中国馆用花、香、酒、药、茶五种味来呈现“弥漫”的意象,正如中国馆策展人彭锋所言,此次展出的5件观念装置作品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分别以荷花、中药、绿茶、熏香、白酒为题材,与“五味俱全”和“五味杂陈”形成隐喻关系,在总体上创造出一个奇妙的感觉世界。“五味是五行的一种表现形式,既意味着基本味道又意味着全部味道,从而蕴含着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观众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将被中国馆展览充分激活,获得别具一格的心理感受。”
“五味”意象还唤起了威尼斯人的历史记忆。威尼斯是香水的发源地之一,作为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也是欧洲从中国进口香草、香料和药物的首要通道。
分有“五行”的“五味”,企图囊括中国文化中的五个基本元素,难怪外媒评论此主题具有文化侵略的意味。在西方人看来,他们虽然流连于作品“云蒸霞蔚”的视觉效果,朦胧体察到东方文化“柔软”的力量,但毕竟不解其中三昧。首先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原弓的《扩散》用的是干冰。原弓确实想到了干冰,但干冰太贵,因为经费问题,在工程师的帮助下,最终选用了大功率加湿器。其次,西方评论家将气的弥漫理解为“Invasion”(入侵),但中国人很清楚,“气”是“道”的充盈。“气”的柔软抚慰,是生命诗意的绵延。释家有“象教”,儒家有“诗教”。如果这位评论者将“Invasion”换成“教化”,便理解了东方的“气”。孔子有言:“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文化就像气一样化育庶民。
孔子曾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如果没有“中行”之人,较之狷者,孔子可能更愿意接受现代艺术家这些“狂者”施教。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如何为世界所接受。现有的做法有:在国外办展览,在纽约时代广场做大屏幕广告等等。这些“走出去”的战略,不能说没有作用,但除了给人以财大气粗的印象就是“Invasion”,更不用说他们外国人如何理解画油彩的脸和没有色彩的风景画。在国内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西方学者问在场的中国学者,为什么中国人要画没有色彩的水墨画,难道中国人都是色盲。在场的学者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可就是没法给这位洋女子说清水墨画为何没有色彩。一位学者拍案而起:你等着,我会写一本书来回答你。可惜,这位有血性的学者兼画家“出师未捷身先死”。如果这些学者多一点“侵略性”的话,应该劝这位洋女子来中国学习十年中国画再说。去欧美展示中国艺术类似上述行为,难度更大的是不能劝众多的观众来中国学习十年再看展览。
另一层原因,西方文化信仰“更快更高更强”,如果不能在感觉强度上取得绝对优势,温柔敦厚的斯文并不能给国人以半点尊严。此次“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被某些西方专家评为最有影响的国家馆,说明五位艺术家的作品的创新具有足够刺激西方观众神经的感觉强度。待到北京成为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城、19世纪的巴黎、二战以后的纽约时,我们才有可能对西方人实施“诗教”。
二、思与境的相遇
本次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北京大学美学中心教授彭峰在6月25日与媒体的见面会上说,如果再选择一次方案,他还会选择“味”作为主题,因为他生活在中国,最了解中国美学。艺术家们却因为环境的原因,不得不改变和修正既定的方案。潘公凯先生的方案需要大型的制冷机,但经费不足,他只能使用几台小功率的制冷机,现场感觉要差一些。如果有厂家赞助大型制冷机,潘先生的作品可以让观众用肌肤感受凄冷的意象。杨茂源的药罐,观众是可以拿走的,几天之后,五千个药罐便让观众收藏完了。如果有经费做50万个药罐,便有50万个观众收藏。他们带着充满中国气味的小药罐从水城威尼斯走向世界,也让中国气味弥漫到世界各地。梁远苇的酒瓶,因为没有足够的二锅头,几天后便没有了酒味。如果有足够的二锅头,每天换一瓶,且雇一个人负责防火,则中国的酒香至少可以在威尼斯弥漫近半年。原弓的《空香6000立方米大于6000平方米》水汽裹着燃香,只要燃香不受潮,尚能展示到结束。生活大概有一条不变的理论:生命的冲动总被境遇所修正。反之,境遇也会激发出生命的潜能。本次双年展留给五位艺术家的创作时间只有两个月,这些装置作品与架上绘画不一样,不在现场安装调试好,便不能说完成。军械库的空间,原弓号称6000立方米,其实面积只有200平方米,除去大储油罐所占的面积,只剩下一点过道了。《环球时报》网站报道:“中国馆在军械库的展示空间,像一个桶的底部,狭小、黑暗,且偏远,还散发着石油的腐臭。事实上,它曾经是一个石油储备库,位于一条业已关闭的工业运河边上,运河散发着恶臭,再加上威尼托大区的水汽和夏天的湿热。”“总之,中国馆的空间给策划人出了一个难题。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相邻的意大利馆宽敞明亮、设备齐全,作为东道主显然有近水楼台之利。”策划人彭峰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的展示条件,刺激了艺术家的创造性,是“更高更快更强”的氛围激发了他们“征服”的欲望。
三、硬与软的相遇
用“柔软”这一触觉概念来描述中国馆的“弥漫”主题是一种智慧。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通过人的通感,沟通了气和东方文化的温和语义。最柔弱的气具有了最强的感觉冲击力,因为双年展上有太多的视觉冲击。一次现代艺术展览,似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以柔克刚”的注脚,成了太极拳术“借力打力”的类比。评论家Harvey Dzodin、写了一篇题为《弥漫式入侵》(‘Pervasion' Invasion)的评论发表于《环球时报》网站(Global Times):“毕竟,那些外行的评论丝毫不会有损中国馆优秀的艺术品质。对我来说,本届双年展其他馆的大多数作品是完全令人费解的”。接着Harvey Dzodin引用国际美学协会现任会长柯蒂斯.L.卡特的话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馆是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上最有创意的国家馆。他们的艺术理念新颖、作品有创意,没有模仿和复制的痕迹。他们的哲学理念和美学设想得到了很好的实现。……我觉得中国馆是我在这次以及所有其他的威尼斯双年展上看到的最有趣的艺术展示之一。”四、有与无的相遇
这届双年展中,装置和行为艺术占90%以上,架上画只占极少数。年复一年的创新,装置艺术变得“黔驴技穷”,观者也审美疲劳。有评论认为最不可救药的就是意大利国家馆,馆内展出了大量油画等反先锋作品,其策展人维托里奥(Vittorio Sgarbi)是一位憎恨现代艺术的政治家和艺术评论家。美国国家馆入口处的雕塑是一尊躺在日光浴床上的青铜自由女神像,给人的感觉是死气沉沉,缺乏想像力。场馆外摆放着一辆肚皮朝上的坦克,上面放着一台跑步机,一位运动员不停地在上面制造着噪音。另一件作品是让美国奥运会体操选手在木制的飞机商务舱座位上表演常规的体操动作。加上前面提到的《算法》,艺术家们隐晦地对美国的爱国主义、军事主义和消费主义表达了批判和嘲讽。只有获得威尼斯双年展最高奖“金狮奖”的德国馆,展现的已故德国馆代表艺术家克里斯托弗·施林格赛夫(Christoph Schlingensief)的生命体验感人致深。中国馆的艺术家原弓的“反装置”作品《空香6000立方米大于6000立方米》和室外作品《扩散》的成功,可以说终结了装置艺术。整个威尼斯众多有形的装置艺术作品被飘渺无形的“气”诠释殆尽,全部的色相被“气”的意象统摄,无数的“有”归于“无”。就像毕加索终结了油画,杜尚终结了艺术一样,装置艺术如何逸出“气”的笼罩?五、殊与和的相遇
以民主和自由作为普适价值的西方现代文明,其艺术是数理哲学的逻辑延伸。数理逻辑要求日常语言与数学语言一样准确和清晰。但艺术的清晰意味着终结。杜尚的《蒙娜丽莎》、《小便池》、《甚至新娘也被光棍扒光了衣服》,其精妙之处正在其复杂而游移的意象结构,作品的语义在杜尚的精心设计下,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然而,杜尚的作品语义只是诸意象结构的发散造成的。此次双年展的美国馆有一件作品《算法》(Algorithm)是取款机与管风琴的组合。作者有意让音乐和货币、古代与现代这些对举的意象产生天然的离心力。德国馆获得本次双年展的“金狮奖”,代表画家是去年去世的艺术家克里斯托弗·施林格赛夫(Christoph Schlingensief)。大厅中央为其作品《恐怖教堂》(“A Church of Fear vs. the Alien Within”)是一位天生的反对派,对德国政府政策几乎一概否定。艺术家生活和作品是一致的,他以反对来确立自我存在的边界和价值,以死亡来赋予生的意义。潘公凯先生的作品《融》用水墨败荷、投影的冰雪光效、-5℃的环境温度和荷花的清香综合在一起,用多个不同的意象来营造清冷、萧瑟的整体艺术意象,各种意象在潘先生的设计下产生了向心力,彼此得以丰满的加强。可以说,这是对“和而不同”的艺术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