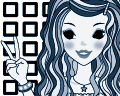在它眼里,我肯定又老了一圈去年从它身边走过的人已是失去的一部分但在我的眼里,它婆娑的神情肯定不知秋天也老了一层虽然它一半的清香已被秋風吹散它心中还是那个少年,面孔写满青涩想念里依然明月挂枝故事刚刚生长,有人未曾离开...
榆钱也是钱,可以换回小梅手里花花绿绿的糖纸可以换回她笑声里的铜铃铛和目光上高掛的甜蜜那时一把镰刀就可以勾下一大片的快乐撒落的榆钱刚好能覆盖童年那时树下用泥巴垒起的城拥有一整支蚂蚁的军队那时什么都是崭新的什么都可以推倒重来那时小梅还是青梅,刚刚绽出...
李星再没有那么好的苇篾了它能划破我的手指而不至于太深它能让我的眼泪充满眼眶但不會流出来我的委屈和疼痛不大也不小我的撒娇声刚好让编苇席的母亲停下来再没有那么好的苇篾了它温柔地绕过母亲粗糙的手指将一个个日子铺展平整再没有那么好的苇篾了它腾跃在母亲怀里...
黑土、红土、灰土、白土构成你的本色。那些青稞、土豆燕麦、油菜和树木杂草填满你的空白和饥荒天,在头顶湛蓝,也在水中浑浊一场雨,洗净高原的心灵就有一场雪,在银色的风中抱紧万物颤抖的,微弱的身子一头黑牦牛的眼睛,打捞并收藏着易逝的事物,有时明亮,有时灰...
风一吹拢云,雨滴就落下来敲成你身上厚厚的棉衣风一拨开云,阳光就洒下来溅起你额头细密的汗珠一朵野花,从冒气的牛粪上探出头我们就萌生了对人类偏执的认识比如高贵与卑贱的身份一个人突然离开了,消失了而我们却无动于衷,像一株锋芒毕露的青稞藐视一簇被母亲拔掉...
东山顶刚暗下去,月亮就升上來篱笆院内,月光照见瓷碟和一小瓶蜂蜜三张稚嫩的脸,像一颗颗刚挖出的土豆挤在一起,硬是将贫瘠的生活挤出满脸的富有和沁心的甜三十多年了,土豆走出山沟,进城娶妻生子,安家落户。一部分事物开始明亮比如月光下回家的路和篱笆院外的水...
在高原,风是我们的骨骼有着无形的坚硬,雪是肉身之外的另一群我们,如影随形有着无可替代的品质山河依旧,唯草色发白它们和我们,彼此制造了生活的两个面有风时,我们活成风的模样无风时,我们活成陌生的一群人鹰在天空,忽略飞翔之外的事物被撕碎的云,不分白昼和...
暮色低垂,送灵的人走出很远了唢呐里吹出的身影,顺风或逆风都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方向那片白,被众人举起。在半空与暮色汇合,彼此交出最后的信任风,像一个漩涡,收藏了所有肃穆的表情摇晃的火焰,送走最后的温暖留下白,化为土壤的另一部分黑滋生一种悲伤的,腐朽...
当我写下:亲爱的这泛滥的,贬值的,腐朽的三个字我就无法继续像雪一样漫溯但雪,就落在屋檐上,院子里觅食的灰雀,无视天气和季节她,始終没有放弃拥有食物的任何机会黄昏没有界线,雪是高原的过度句读一句,就老去一截。直到一盏油灯,被点燃,光圈里天末凉风而雪...
月亮把头伸进我的窗子它的眼神比我的蚊帐还要白白色打破了幽暗的秩序忧愁的人难以入睡在狹小的室内打转这异乡的生活虽然愉快但家更有吸引力出门随便走走看看远方,不知不觉又回到房内……那些无法说出的话无人倾听的话只能让眼睛去说让盐去说让衣襟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