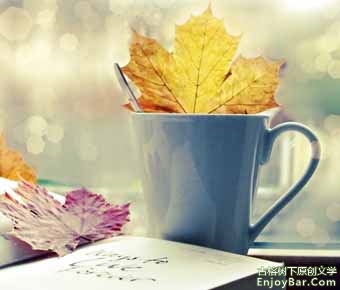影响我的几本书
对于一个读书者,而且未经岁月的历炼,而侈谈影响者,实在是有些不合适的。所谓影响,也必有影响而谈之。倘若单单读了几本书,而大谈影响以助门面者,亦不免流于浅薄,必为大方之家所耻笑也。
然则必若宿儒而谈之,亦不免矜持太过。我自有影响,不妨据实谈之,虽然未必有真知灼见,也不失于真实。如此,便无过矣。
但现今之文章,除了报刊味外,相互吹捧者为多。亦或为了装点门面,而侈谈影响以失真实,实在是文章的悲哀。更有甚者,有些大人先生,借自己的声名以掩文章之弊,而堂皇刊于报刊,为众人所仰慕。倘若揭去声名的遮幕,单以文章优劣而论之,则与裹脚布无异。
文章重在有味,何为有味,意于字外而流布行间,不失真实,则必为好文章。但是现今文章有味者实在寥寥。这固然是时代的趋向,但更重要的,是不学文章导致。
影响我的,主要有下面的几本,容我一一说来。
一、东坡词
东坡词,倘若一言以蔽之,必是王国维先生所谓“旷”。旷者,达也。达乎天命,而随天地造化以自适,实在是大苏最可观之处。大苏一生,可谓坎坷而多舛。辗转流离于杭、密、徐、湖、黄州间,最远到海南,加之妻子早逝,人情的冷暖与世态的炎凉,便体会得尤为深切。换作别人,将不免抑郁伤怀。毕竟历史上不乏其人。贾谊即是一例。但大苏独能在这许多困顿中潇然自适,落拓无羁,坦然面对人世和命运的浇漓,这实在是难能而可贵的品质。且让我们听听他的心声。“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大苏之词,须如茶,品之则其味无穷。令人在清景之外得一份精神的慰藉,而能坦然面对纷离的世事,于人生的苦境中扬起信念之帆,这实是难得的快事。
然而大苏亦非没有困扰之时。在他的落拓和旷达中,常常掩抑人生的无奈与虚空。如“君臣一梦,古今虚名”、“人生如梦”、“世事一场大梦”、“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只是大苏将苦闷很好地排遣,以旷达之怀坦对人生的不幸与困苦。
二、知堂散文
倘若必问我现代文中最喜欢谁的文章,我必说是周作人先生和梁实秋先生的。梁先生的散文,清浅中韵味无穷。文字虽澄澈,但澄澈中不乏文采与韵味,咀嚼之,则欣然不能自已。诚如他所说的“萝卜汤”。最难能可贵者即是他常常以学者式的幽默入乎文章,足令人喷饭却没有媚态,而矜持持重,不失身份。比之于老舍先生的文章,老舍先生的文章活泼有余而稳重不足,虽然常存幽默之言,然而不免矫作的痕迹。
周作人先生的文章于我影响最深。我的文章难脱模仿他的痕迹。其文章朴素真实,一派自然淡雅之气,绝没有涂脂抹粉的痕迹,如他所说的美人,不饰脂粉,以天然的面目面见观者。故而其文章基本不用藻饰之词,娓娓道来却蕴味无限。
读先生之文,宛若食肉,咬之则紧凑有味,须细细啖之,慢慢咽之,方能得其旨髓。而此种风味,有赖于古文的功力,功力不济,则不能达此境界,故而不易学。这也是学周作人先生的散文容易走样的症喉所在。
先生之文,不避琐屑,独能在琐屑中见出长处来。他所言之事,皆是身边小事,但是却又贴切真实,令人信服不已。
但凡先生的文章,我都喜欢,尤其《知堂回想录》,令人读完之后遥想其味。我独不喜欢者,是他评鲁迅先生的小说的那本,从其姿态中可以见出未免有轻率之嫌,不仅杂乱,而且一扫平常的韵味,实是周先生的败笔。
三、《沉思录》
此处所说《沉思录》,并非马可·奥勒留那本,而是爱比克泰德的《沉思录》。爱比克泰德先于奥勒留,他们有师承关系。斯多葛派哲学经爱比克泰德到奥勒留便集大成。这一本书主要讲人生的哲学,即为人处事。
爱比克泰德认为,人生本没有意义,应将人生视如赴宴,在其中举止应优雅得体。对子女、伴侣、职业与财富,也应同样保持优雅。一个人应该追求宁静、满足、自适的生活,顺应天意,遵从天命,并且一生都追求美德,将内心之恐惧、欲望、恶意、贪婪、娇气、放纵除去,保持植入内心神性的完满,以达自身的完美。
爱比克泰德强调理性和节制,以为人之生活,亦应听凭理性的调遣,在任何事上都须慎思明辨。他强调人应过一种节制的生活,养成良好习惯,并始终遵从如一,不论天气好坏,不论周遭发生什么事,都须坚持到底。
此外,他还提及有效避免痛苦的方法,即区分什么我们能控制,什么不能控制。对于可控之事诸如欲望、意志,则使之符契宇宙的意志,遵从自然的秩序,不与天命相悖。而之于身体、财富、子女、权利、声望等,则任之自然,不予关注。人应就天命所赐而适性随意生活。
四、《蒙田散文》
接触蒙田散文,是得季羡林先生的濡染而始知道蒙田的意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盛赞蒙田,以为当今之散文者,须效法蒙田而得其精髓。他认为当今散文抒情有余,而说理不足。我的读蒙田,也是在这以后很久的事。虽然读竟,对于他的道理也还是一知半解,故而不能深度挖掘其要义,仅以粗浅的转述聊供赏阅。但我认为蒙田确实写得好文章,这不光是说他说理精辟,文字也确实漂亮,很多比喻。当然这有赖于译者的功力。我所读的是梁宗岱先生的译文。我认为梁宗岱先生的译文,也足以为散文界之冠冕,味淡而隽永。
翻译的文章中,很少有令人满意的。这主要是译者只精通外语,而对于国语粗疏之故。在译介中,能做到译文之卓然斐然,令人百读不厌者实在寥寥。就我所读的译文中,朱光潜先生的译文、梁实秋先生的译介是很令人满意的。而当今的翻译界,能译出好文章者实不多见。这或者是我孤陋寡闻之故。
蒙田也同爱比克泰德一样,注重理性、品德与节制。强调自我审查的必要,认为知识和钻研将使我们的判断力低下,使心灵胶滞。他认为我们须退隐到自己的灵魂里,经常的与灵魂晤谈才能得真自由。而依赖妻子、财产则会使人产生痛苦。但归隐在自身里的前提须是灵魂的足够强大。倘若不能自抑而轻信于己,则会有失足的危险。而灵魂的特点即是,倘若没有一定的念头占据内心,则可能长满野草,使自己迷失方向,因为无所不在就等于无所在。
蒙田认为哲学的要义即是学死,他认为死是宇宙的秩序,是生命的使然,人在生着的同时也在向死亡趱程。而畏惧死是人的天性。而且,宇宙间的事物,有许多的重复性,一日也就是一生,你祖宗享有的也将传给你的后裔。何况寿命与人都不是可以用尺量度的。因而对于死不应该畏惧,而应常常想到死。
此外,一个人须生活得写意,至如权利、财富、产业,亦不过写意的点缀与附属品。故而不应太过重视。他奉劝人应该从繁琐的世事中摆脱出来,拿得起,放得下。
五、《忏悔录》
倘若人类自存在以来还有真人的存在,那么卢梭便是唯一的一例。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不论伟人或是小丑,都试图美化自我的形象,因而表面的遮掩下往往隐藏另一个人。他往往是我们真实品质的缩影,其间不乏自私与邪恶。因而社会中的人,只能算得半个人,而非全面的自己。
然而卢梭则不同。又有谁敢如此大胆自剖并示之于人呢?没有人会自叙自己的小偷行径,即使小偷本人。然而卢梭却毫不避讳,他在回忆自我经历的同时也在拷问灵魂,把自己的恶彰显出来,因为他觉得没有可憎缺点的人是没有的。
卢梭给人最深的感触即是真,即在任何事情上都力求真实。他仿佛人的一面镜子,照见美德时亦显现恶。
卢梭生于日内瓦,父亲是一钟表匠。他曾做过学徒,学过音乐,也曾做过法国驻威尼斯公使的秘书。后来留在巴黎,三十八岁时以一部音乐剧《风流韵神》出名,之后退居退隐庐,写有《新爱洛漪丝》、《爱弥儿》、《忏悔录》等书。晚年遭法国人斥逐,定居瑞典。
六、《老人与海》
倘若在人生的逆境中,没有一种坚强的品质,是很难自立并坦然的,痛苦将以不测的面目莅临我们。故而精神实在是人生最必要的支柱。倘若我们耐得住折磨,并且正视人生的困苦,以不屈的姿态迎击命运的浇漓,则此种精神必然使我们永远屹立,即使死亡也不能消灭痕迹。《老人与海》是此种精神的楷模。
老人在捕鱼时经历了一系列灾难,但这灾难终究是冶炉,炼就了老人不屈的铁骨。“然而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老人的悲剧意义在于,他在人生中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失败得如此残烈、如此悲壮。而这悲惨的境遇,愈加衬托了老人精神品质的可贵。他似乎在告诉我们:即使你输得残烈,也应屹立。此种精神,便足以熔冶人生,使它就范于我们自己,而使我们终能成为主宰。
显然此种精神是源于对古希腊精神的传承。这可以由《老人与海》与《奥德赛》的相似性中得到证明:老人失掉了大鱼,奥德修斯失掉了所有同伴,他们在人生的境遇里遭遇灾难,但他们都不曾屈服,即使败得很惨。
此种精神,应是我们所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