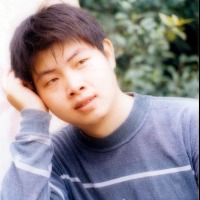在巴黎高师,萨特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几年光阴。他在这里感受到充分的自由和独立。
学生是两三人一个房间。尼赞和萨特共居一室。后来尼赞去亚丁了,萨特一个人一个房间,在里面休息和学习,很是安静自在。学校里对学生管得很松,他们有充分的活动自由。夜里回来得很晚也不要紧,可以随便翻墙而入。这样的自由很合萨特的意。
这里的学术空气也很自由。教师和学生中,从宗教神学到马克思主义,信仰什么的都有。大家的思想都很活跃。但是,没有任何人去干涉别人的思想和信仰自由。萨特的朋友,有不少人信仰社会主义,还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如尼赞就参加了共产党。萨特本人不信仰任何主义,这些朋友也从来不同他谈这方面的问题。他觉得这样很好。
现在萨特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这是他最感欣慰的。学校住宿和伙食都是免费的,每月还有少许零用钱。这样他再也不用靠家庭供养了。每星期萨特回家一、两次,与家人共进午餐。
这时他同继父的关系反而得到缓和。对方不再是自己必须依赖的对象,不再是烦恼之源;在萨特同父母之间,慢慢有了一种家庭的温情。萨特终于从“偷钱事件”的阴影中彻底解脱出来。
在家庭关系开始正常化的同时,它对萨特也不起什么作用了。萨特现在完全生活他所在的学校和伙伴之中,更多地成了一个社会人。
巴黎高师的伙食并不好,萨特很是讨厌。他希望能在外面吃饭,至少能在咖啡馆喝喝咖啡。有时还要看看电影。至于上剧院、听音乐会,那就是更高级的享受了。而这些都得另外有钱。
萨特同学中有不少人干家教的活,辅导那些学习成绩较差、跟不上来的学生,通常是读二、三年级的,让他们能够赶上来,最后通过毕业会考和考上大学。
萨特也干起了这个。除了吉尔介绍的那个莫雷尔夫人的儿子外,他还接了其它一些活,主要是教哲学,也教点别的,比如弹钢琴什么的。
讲一小时课他大概可以获得20法郎。他并不认为这是真正的工作,虽然他讲起课来十分认真。“赚这笔钱简直像玩儿似的!”他看着手中的一叠钞票说道。
由于小的时候受外祖父查尔的影响,他看不到劳动与报酬之间的关系。小萨特常见查尔有大笔的钱进来,却没有看过他是怎样工作。他以为查尔的工作就是请他的学生来吃饭。
萨特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闹清楚过这两者的关系。他酷爱写作,献身文学,但这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却可以得到钱财,这是他难以理解的事情。
以后成了有名的作家,萨特常能拿到大笔的钱。但他仍然对自己的书和钱之间的关系困惑不解。特别是一本小说或一个剧本已经出版许多年,由于国外的译本或演出,他突然收到一大笔版税。看着一张张大额汇票,他想:“我真的应该得到这笔钱吗?”
因为觉得钱来得容易,花起来也就不当一回事。萨特是有了钱就花,从不去算计,而且不是一个人花,是同朋友们一起,在饭馆里用掉他刚拿到手的最后一分钱。他在巴黎高师,很快就有了慷慨大方的名声。
特别是同姑娘们在一起,萨特更是不在乎钱,显得很有绅士风度。以后他有了大笔的钱时,花在自己身上的其实很少,绝大部分都是给别人用了。主要是一些女人,他所喜爱的女人。有的女人,他供养了她们一生。直到晚年,在他临终之时,他还在惦念着自己的钱不够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要养活的那几个人。
萨特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慷慨,他对于金钱没有任何占有的概念。这也难怪,自小他就没有占有过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归他所有。这一点使他在钱财问题上超出了一般人的观念和态度。
在他看来,金钱除了供人获得他需要的东西,不具有其它的意义。它只是获得需要物的凭证。既然如此,如果别人也需要这些东西,那就可以共享。萨特几乎没有任何私有财产。他从来不购置任何东西。在他已经比较有钱的时候,他住的公寓,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别的东西。作为文化人,甚至也没有什么书。
如果说萨特也占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占有词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放到这上面。而这是给予,是奉献,而不是得到和索取。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萨特都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