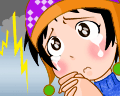王延龄最近读了吴晗同志遗著《江浙藏书家史略》,很有点感慨。这本书是他青年时代读书笔记,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辑录了江浙藏书家的历史。可见他治学始于博,而后在博的基础上专研一门成为一代史学家。可是读完了这本书却感到藏书家的辛酸是和他们生活的时代分不开的...
给黎之同志的复信黎之同志:您在《读书》杂志今年第二期发表的给我的信,对我的学步之作给予如此热诚的关怀,读后感激之至。这部稿子的成书过程,您比我更了解。当韦君宜同志把我的初稿带回北京之后,先后有八位同志传阅,参与推敲。为了支持它的出版,惊动和烦劳这...
李君维等这是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者迈克尔·斯卡梅尔(MichaelScamel1)是当前英国一个很活跃的作家。“布隆斯伯里”(Bloomsbury)是伦敦中西部的一个区域的名字,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即位...
狄兆吕叔湘同志最近在《读书》上两论错字,由此想到另一种刺眼的错字:汉字中间偶尔杂用的英文词句,常常印错。下面举两个例子。“今天早晨进厂,挤上公共汽车,前面有一位军人,我对他说:‘goodmornjng!”(《人民文学》一九八一年八期111页,其中...
许力以包之静同志一九七一年逝世,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他去世时五十九岁,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只有五十四岁,这正是精力旺盛,而又富有工作经验的年华,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但是可恶的“四人帮”,却夺去了他的生命。象包之静同志这样好同志,被迫害至死的,何止一个。...
瞿林东一封关于读书会的信去年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白寿彝教授的一封信。这是一封打印的信,全文是:“×××同志:“多年来,我总想有个经常性的机会,大家谈谈读书心得,交换对于新书刊的意见。我想,这对于开扩眼界,交流学术见解,推动学术工作,都有好处。...
郭殿忱《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二期所载散文《致尕斯库勒湖》描述地下的石油说:“大漠底下却不住地喧闹着,终于酿就了一条灿烂的黑金的河流。”这是欠准确的。地下的石油含在油砂中,根本不是“黑金的河流”。希望作家多学一点自然科学,不要成为“科盲”。...
刘九如《读书》一九八○年第九期《陆游和》文中说:“陆游的二儿子陆子编《陆游文集》时也说……。”同一作者在《老学庵笔记》一书前言中,把子称为“陆游幼子”。看来,作者是误认为陆游只有两个儿子了。其实陆游共有七子。《陆游年谱》中有记述:长子陆子虞,次子...
舒昌善读尤·库岑斯基的文学评论《外国文艺》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刊载了美国利茨(A.WaltonLitz)的一篇论文《“新批评派”的衰落》,译者董衡巽同志在前言中写道:“‘新批评派是美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在这个庞杂而无形的集团中,批...
毛韵泽“十年寒窗”,大家都知道它的含义,而“十年铁窗”,恐怕谁也不会指望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什么成就。但如果你读一读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的传记,就会知道,震动西方学术界的《狱中札记》就是葛兰西在“十年铁窗”中断断续续写下来的思想片断。这本书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