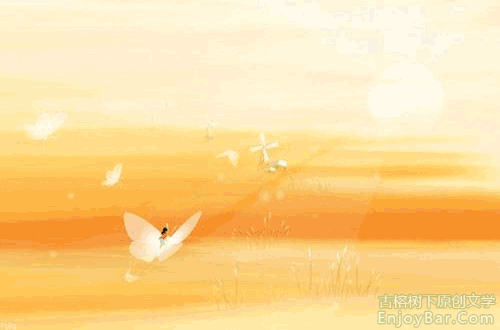那个白胡子老人下船之后也没有和别人打招呼,他便顺着大坝下的另一条通往滨州方向的小路,独自一个人默默的去了,也没有人知道他当时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更没有再多的人知道刚才在黄河渡船上的那惊险又让人费解的一幕,阿傻的父亲也想不通,他只是最后看了一眼那老人慢慢离去的背影,心里骤然想起了自己早已离开人世的老父亲,他心里真的不是滋味。抛下那老人暂时不讲,再说阿傻的父亲。
“人呐……转眼的功夫……就老啦!唉!”
他这句在心里的话大个子并没有看出来。
下了那黄河主坝再翻过两道副坝这才整儿八经的踏上回家的路,路上无话等到他们各自赶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了。
夜深了,初春的夜里,那个不大又穷困的小村庄让那冷飕飕的风一吹,显得格外凄凉,远远望去就好像个早早被人遗弃不知有多久的部落。家家户户早已熄了灯,坑坑洼洼的街道上黑乎乎的,就像一个看不见头的黑洞子又窄又长。
阿傻的父亲来到自家院门前把车子轻轻地一放,伸手轻轻推开了那个破旧的木栅栏门,他又重新转回身弯腰双手端起车把,把车子慢慢推进了院子,在靠近屋墙根底下地方小心地放了下来,他动作很轻他还怕惊醒了屋里早已睡熟了的母亲和自己的妻子。放下车子他站在那里轻轻地长出了一口气“唉!终于到家了!”在心里他默默的为自己开心。大门还没关他又转回身轻轻的走到大门口慢慢的关上了那扇“大门”,他不想吵醒屋里熟睡的人可……屋里的人还是听见了,就在他小心的拿手轻轻去推开那两扇厚实的屋门时,干燥的门轴执拗一响,他那颗自我埋怨的心禁不住让他身子稍微一怔,迈步刚要往屋里走。
“谁呀?”
屋里紧接着便传出一个很憔悴的声音。那是阿傻的母亲刚才门轴的轻轻一响并没有睡着的她听见了。
“我——你还没睡?这刚回来喽!”
听自己的妻子还没睡,阿傻的父亲站在外屋便答应了一声,而后随手把门一关迈步便进了屋子。
妻子听是自己的丈夫回来了,她赶紧穿上衣服下了炕,在桌子上摸起火柴点着了那盏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悠悠的闪着火花,来到屋里感觉浑身暖和多了。
“你浑身都是泥水……冷吧?快拖下来换换我去给你烧点水你喝喝暖暖身子!”
“啊!孩子和咱娘都睡了?”
“嗯……睡了!”
“这外屋怪冷的别去烧了。”
“不用,一会就烧开了,你换下衣裳坐那等等吧!”
“这几天家里没啥事吧?屋顶没漏雨?”
“没有,村里开活了!”
“今年开的早,我看着以后那线你也就别再纺了,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再熬夜纺线我怕你身子受不了。”
“没事……纺点线还能多挣点工分不是?”
“……!”
听了妻子那很坚决的话阿傻的父亲再也没有说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他心疼妻子可眼下吃穿不保的日子,他的心里好难受好矛盾,脑袋瓜子乱乱的就像一团解不开的麻绳,找也找不到头绪。他换好了衣服静静地坐在炕沿上,立时觉的浑身上下软的就像一块棉花,双眼眨眨的好想睡。桌子上的煤油灯那萤火虫样的亮光红红的闪闪的照亮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窗外起风了很大只刮得院中的木栅栏呼呼作响。妻子在外屋的灶前烧水,随着风箱轻轻地拉动屋里越加暖和起来,他的睡意更浓了。
“给!你快喝点吧!喝完了早点睡。”
“放那桌子上吧我先抽袋烟,你早点睡下吧,我等会再睡!”
“嗯!今天早晨老木来了,说是找你。”
“呃?他来干啥?不会是家里的炕又坏了吧?老没(木)板子。”
“他?谁知道哇?他支支吾吾的我看好像是想叫你出去唱戏?”
“唱戏?上哪?不给钱的事不去,哪有这闲心。”
“他说完了就走了,下午天黑的时候还又过来的。”
“嗯!明天吧,明天我过去看看,备不住可能有别的事,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点了,如果是能挣两钱的话出去也无妨,今天我在黄河……。”
不知咋的阿傻的父亲欲言又止,本来已到嗓子眼的话他又给咽回去了。
“到时候你想去你就去,家里的事有俺和娘,只是队长王二愣那,我觉着你得去给人家说一声,毕竟你现在还在队上干着队长呢?总不能把啥事都推给人家吧?”
“嗯……我知道,苦日子算是过去一半了,我这队长也算到头了,等有机会我找到老王辞了就算了,该换年轻的了。”
“不干不干吧,看当初种地的时候把你忙的那个样、愁的那个样,整天跟头咕噜的连口热饭也吃不上,能辞就辞了吧!”
“嗯!……你睡吧!”
“嗯!”
两人的对话声音很轻,他们怕惊醒了那屋里熟睡着的母亲和三个孩子。
阿傻的父亲坐在椅子上足足抽了两袋烟,低头一看那碗里的水已经温凉了,他爸烟袋往桌子上一放,伸手端起那碗水一口气便喝完了,把水碗往桌子上一推而后便脱了鞋子便上到了炕里,妻子见自己的丈夫那般劳累,她躺在被窝里侧着身把炕头的纺车又使劲往里推了推,而后回身吹灭了桌上的煤油灯……
老白姓的日子就是那么平平淡淡、平淡的像那碗白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