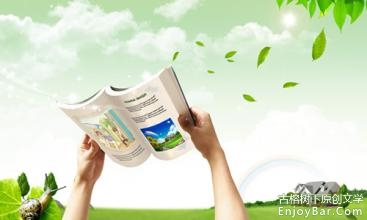我妈又一次逼我去看人的时候,我没有说什么,就跟上表姐夫走了。
妈说:“也不换换衣裳?”
我不说什么,只是走,走出屋门,让日光明明白白地照出我这身打扮的旧。
妈又叮嘱:“正里八经的。”
我仍不说什么,走完了带子似的小院,拐进了过间,整个身子投进了灰暗里。
妈追出来叮咛:“有点数。”
我就没好气地回了句:“你放心得了,这一回保证把看人钱花了。 ”说完这话,我扭头看了一眼妈,见妈的嘴唇有些抖,我的心就也很苦很痛地抖了,抖得一紧一紧的。我想,为了我妈颤抖的嘴唇和我颤抖的心,我无论如何也要定个媳妇了,只要“她”肯,我就肯;即使她没有浓秀的眉和美丽的眼睛,即使她不会柔柔地一缕小风似的说话, 即使她不会斜挎了脸盆微侧了身子把鬓发抿一缕耳朵后面露出姑娘端正的耳轮……
表姐夫把我搁在一个小屋子里就走了,他的脚步声很急很重地响了一阵便消失了。他在这村里蹲点蹲得很久,村里的街道一定很熟悉了他的脚步,他这才能够给我说个媳妇。
我在这屋子里等着。这屋子真古老,梁檩和椽子都乌黑透着点暗红,唯独屋笆是新的高粱秸,比照得很强烈,很醒目。窗户也很古旧,木棂子很壮实,很牢固,我想要是有人从外面把门锁了,要砸窗户出去不大容易,这么想着我就生起了一种被关起来的感觉。我的心被压得好紧,长长地吁气也难松动。
我艰难地等着。后来听到街门响了一下,接着有了脚步声,接着有一个妇人的声音,说:“在家?”
我想这是问屋子的主人了。我就起身,把屋门打开,迎上那声音,说:“来吧。”
妇人和我就都把对方看了。她是个很高大的妇人,除了胸脯子那里垂下两坨以外,其他地方都很像男人。眉眼没有什么特征,只有两只嘴角白得很突出,像是被唾沫什么的沤烂了。我不知道我被这妇人看了什么在眼里,我看到她的就是这。就在看的同时,她说:“来啦?”我说:“啊,进来坐吧。”她说:“不了,我寻思来借个簸箕呢。” 我说:“你知道在哪里就拿吧。”她再看我几眼,就去西厢屋里拿了簸箕走了。
脚步声远去,我暗笑了。“借簸箕?”我可不是第一次看人了。就从那双美丽的眼睛和浓秀的眉远我而去以后,我这是第四次看人了, 哪一次大都在我真正要“看”的“人”来到之前,会有个老的或不十分老的妇人来看我,其实也是叫我看,叫我从她老旧的面貌上看出一点年轻的影子,于是在我心里先描摹出一幅与要“看”的“人”大致差不多的图像,从而生起好感或恶感,希望或失望……现在,这位“借簸箕”的老妇人就让我生起了恶感和失望,可是……
不久她来了。果然真大,好在嘴角没有白……
看人回来是傍晚了,村子已经笼了炊烟的纱。有狗在村子里乱跑,还有孩子们乱喊。有个孩子喊着跑着撞到我的怀里,咯咯地笑着扭头又跑了。
进家我妈就看我的脸。我知道我的脸沉得很紧,因为我的心沉。
妈小心地问我:“什么样?”
我说:“尽管把钱给她了。”
妈的嘴角牵动了一下,牵出一丝笑来,转而又消失了。
我仰躺到炕上。没有铺草的土炕和炕席紧贴着硌我的后头,我把胳膊倒伸回去,两手托住头,让手背和手指头关节替后头挨硌。
妈说:“不好啊?”
我说:“好啊,不好能给她钱?”我爬起来,还想说句什么,见妈转过身去,快步走出了炕间,我就闭了嘴。我不能再折磨我妈了,她怕我打光棍,着急,这有什么错呢?说媳妇,吹过一个,还不如原本就没有定过,好,人家为什么跟他吹?
就要她吧,那个大大的人。听说,她也是被人吹过的,吹她的是个小军官,要她的时候,军人的军装两个兜,等到穿四个兜的了,就吹了她。她那么大的人也能被人吹倒,听说,她大病过一场的,为那事。
那么就这样吧,两个被人“吹过”的男女,合到一起,组起个家来。家里该有安宁和幸福的,只要有个勤谨温柔的女人操持。可是,她会温柔吗?她那么大,除了耸起两坨胸脯,其他的地方都像个男人……我痛苦地摇摇头,眼前亮起一双美丽的眼睛,浓秀的眉直渗向鬓角……
不久,她来我家“会面”了,我从村东头那间做教室的屋子回家,街上人叽叽嘎嘎地笑我说我:
“这一下子来了能干活的了!”
“打起仗来可得小心点儿!”
……
我的脸像被人一左一右地抽着耳光,我硬着头皮咧嘴笑。我想我笑得一定比哭还要难看,我这样子进门,一进门看见的正是她向我迎来的笑脸。她原来也会像个女人一样地笑,可是她为什么不长个女人的身材呢?大而憨,小而娇,你为什么要这么大?
“回来啦?”她说。我已经知道了她的嗓门低粗。
我“啊”一声。
“教学真忙啊。”她说。
我说:“嗯,忙,家里活简直不能干,挑水垫栏都顾不得,自留地也不能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她又微笑了一下,我就看见她大大的身架。她的脸唰的红了,低下头去,捏着她的衣角。她的手也是大的,骨节和手指都很粗大,这是一双做重活的手,不是捏针绣花的手。
我说:“山场的活很累吧?”
她仍低了头捏衣角,说:“累什么,干常了就不累了。”
我说:“人家都说,洼地的姑娘到山场做媳妇做不来,山场的姑娘到洼地做媳妇做得来,常了就变懒了呢。”
“你以为俺想着来享福呀?”她就抬起头来打量我一下,说,“你又不是吃公家粮的,过庄稼日子,不伏下身子能行?”
看样子她一定是很能过日子的,可是,我要的不光是这个,我还要……
我看着她,她也看我,她的眼睛不大,但也明亮,只是被我看得垂下了。她这么不经看。
我说:“去年公社宣传队演戏你看了?”
她说:“看了,你编的?”
我“啊”一声,看着她,我期待着她还说点什么,我正为我小小的成功而踌躇满志,我需要她说,但她没有说。我就说:“我还得回去上课,你在这里耍吧。”我就走了。
我照例也要去她家“会面”。去的时候天阴得很重,乌悠山戴了顶深灰的帽子,山下面她的村子隐了大半。在她家炕上喝酒吃菜的时候下起雨来,时大时小,只是没有间断,也没有要停的意思。屋子里的昏暗渐渐变重,云后头的日头该落了。我急着回家,她妈和她爹都不让走,我坚持要走,她妈就大声地说:
“不愿住就走吧!”
我不禁颤了一下,那声音的大正如那身子的大,全不像一个女人,像个大汉,使人感到一种威严和震慑。我斜了眼看她,见她正用眼睛说我:叫你住你就住,硬走不惹人火吗?我只好不走。
晚饭以后,雨稍稍小了些,她拿了手电筒送我去睡觉的地方。她亮着手电筒走在头里,我跟在后头。手电筒投出的微红的圆光罩着我的脚,我脚上布鞋的白塑料底皎皎的白,渐渐地也就不白,沾了泥水。她的脚在黑夜里,我不知道有没有白塑料底,只听得清亮的溅水声,我跟着她走过南北胡同,走上东西大街。大街自西向东渐渐高起,铺了石头。往西走,她就比我矮了。我想她要是长成这样就好了。街上很静,只有淅沥的雨声和我俩的脚步声,脚步声引起低低的回音,愈显出雨夜的静。
“水湾。”
“石头。”
“拐弯。”
走在头里的她不时低声地提醒我。她的声音放低了,虽然很粗,却有了几分温柔,我想她要是总这样说话也许会好。
睡觉的地方是她家的一个闲屋子,灯亮起来以后,我看到炕上已经铺开了被褥,不新,却很洁净。她把手伸进被窝里试了一下,说:“你睡吧。”看也没看我一眼,就匆匆地走了。
我躺进她用手试过的被窝里,我没有什么感觉,身子木木的,心里空空的。忽然间又觉得什么滋味都有,心里乱乱地满了。窗外雨声淅沥,屋檐上下来的水落在地上,发出浊浊的钝响。听远处,唰声一片,我想那该是乌悠山上的松树在雨里集体作响。我想起了山腰处那片残破的屋垣房墙,那里本有座庙宇,住过和尚。在那堵短墙外,有一眼石井,原本有很清冽的水,那水把和尚们滋养得很精神,唇红齿白,头皮光光地亮。后来人们发现,深深的庙宇里藏了年轻的女人,就放火烧了庙宇。这不知是哪年的事了。现在,那小井的水仍有,只是,将要被泥石腐草填满了。
我迷迷糊糊地上山去,脚下踩着一个挨一个摆好的蒲团,蒲团包着褪色的标语纸,里面包的什么不知道,很厚,很松软,踩上去,身子一颤一颤的,像要悠起来。我想着,很得意,脚就落得重了。忽然一脚下去,蒲团踩破了一个,整条腿陷下去……
惊恐中醒过来,听到窗外有人低低地叫:“起来吧。”扭头看看,有个高高大大的身影印在窗上。我一挺身子坐起来,窗外的身影倏地消失了。
吃了她妈做的早饭,我回家,她送我。
雨已经停了。天却没有要清起来的意思,乌悠山仍被云雾遮住大半,灰的云黑的云从山顶山腰上飞快地掠过。天空的云散开的散开,聚集的聚集,这儿薄了轻了那儿又厚了重了,整个的天仍然显得沉重郁暗。路是泥泞的,我的鞋白塑料底早已不白,黑鞋帮也已经不黑。我就这么不黑不白地走。
她仍走在我的前头,步子很大,走一会儿意识到什么就把步子放慢一些,回过头来看我。
“叫你换鞋你不。”她说。
走时,她妈和她爹都要我穿她爹的雨鞋,我执意没穿,现在她就这么说。
“你为什么不换,怕脏了你那脚?”她说。
“不是。”
“是什么?”
我寻找理由,终于想出:“还得往回捎。”
她不再说了,再看看我的脚。我也看她,她脚上穿的也是布鞋,她为什么不穿雨鞋呢?她该有的,既然她爹有。
过了一个坡,走上了山道,路上沙多了些,路面也有点硬了,就走得轻快了。
我说:“我不该住下。”
“为什么?”
“你不怕被人说?”
“说什么?”
“你说呢?”
她的头垂下了,红了脸颊。转而又抬起头来,摇一下说:“爱说说去!”
“你还挺勇敢呢。”我听出我的语气里含了些讥讽意味。
她唰的扭过脸来,直直地看我,忽的收住脚步,说:“你走吧。”
我愣了一下,也站住看她。我看到她不大然而明亮的眼睛里有紫色的火花闪耀。我有些心虚,同时又有些心烦,再给她一道硬硬的目光,就顾自扭头走去。
“等等。”她叫一声,追来,从腋下拿出个布包来递给我。这半天,我竟没注意到她腋下还挟了这包包。
我拿着包包发愣的时候她转身匆匆地走了,大大的步子重重的脚步一会儿把大大的身架送得远远。我打开包包,是两双绣得很精巧很细致的鞋垫,叫人想到的是一双灵巧的纤手,怎么也不能把那双大手想起。我抬头远望,那高高大大的身影正向着灰黑的云雾里隐去。我的心里骤然涨满怅惘的烟云,迟迟地转回身来,脚步沉重地踏着沙路,心想,跟这个高高大大的女子过日子也许会好。
公社宣传队仍然在演我编的那个戏,那个头上绑了两个把把的知识青年把写了墨字的红标语贴到墙上去,“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山村志不移”,大学坚决不去,说不去就不去,姑娘真的要练成铁的了。戏这么演着,写戏的我却要上大学去了。我为什么不去呢?我奋斗了,贫下中农承认了我的奋斗,把我往上面推荐,上面再推,再推,就一直推了上去,我没有理由不让推的。戏里那姑娘的理由是我硬为她想的,她要是上了大学,我就不能上了。
我上县城去,告别我奋斗的时候帮过我的朋友们。回来的路上,我自行车把向右拐,拐进她的村里,拐进她的家里。
她家里早就知道我要上学了,她和她妈她爹都不快乐。她妈的脾气大得很,满脸罩着吓人的云,好像随时都会有霹雳闪电爆发出来。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说要走,她妈叫吃了饭再走,我说不了,她妈说不吃就不吃,烧点水喝吧,我说不用麻烦了,她妈说麻烦什么,我说真的不用麻烦了,她妈就喊起来:“麻烦什么!什么不麻烦?不吃不喝不麻烦,干死饿死?”
我没有话说,也不敢说什么话。
这时候她说:“烧就烧呗,吵吵什么!”说着,就在灶旁蹲下,点上了火。
我就不能硬走了,她叫我这么做,我知道。
然后是滋啦锅响,然后是啪啪啪敲碎鸡蛋壳,然后是稀里呼噜喝得水响嘴响,然后我推着自行车出门,她送我。
都不说话。
落日正红。西面天空着火,头顶上是红烟紫烟,云烟静静地停在那儿。云烧成了烟是死的,因为没有风。
真静,心里是空的,没有欢喜没有悲伤没有依恋没有怅惘,这也就没有话说。
自行车在中间,那边是她,这边是我。她不看我,看着前面。我看她了,知道了她不看我,知道了她不看我我就不再看她。我心里没有要看她的意思,我不看也知道她的身架是大的,眼睛明亮,但不大,也不美丽。
我终于说:“你回去吧。”停住了车子。
她仍走。
“你送我还不能骑。”
她就停住了。
我走上去一步。
她说:“你走吧。”
我说:“你回去吧。”
她说:“你走了我就走。”
我推着车子向前,我没有推动车子。我回头看,车子的货架上有她的手,她稳稳地立在那儿,眼睛平平地向前看,她的力气这么大。
我说:“你……”
她不看我,说:“上了学,要是人家都戴手表,你就也买块戴。”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只大手来,伸到我的胸前,手掌摊开,手心里躺着捏成了一卷的钱票。
我不接钱,说:“我不想戴手表的。”
“为什么不想,人家戴咱就戴。”
我说:“也不用,我有钱。”
“你有是你的,兴你给我就不兴我给你?”“不。”我往后推着她的大手,我的手触到了火烫般的热。“叫你拿着你就拿着!”她的大手在车座上一拍,像她的妈一样说话,大身子猛地转回去,走了。
钱卷儿在皮子的车座上颤动,颤动,无声地落到了地上。我弯腰捡起,拈开一看,正是看人时我给她的那个数,可以买一块时下流行的“钟山”表。
上学后我给她去了一封信,说学校挺好的,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你放心吧。再也没有别的话。几天后她就给我来了一信,说:“听说学校挺好的,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也就放心了。”别的话也再没有。
我是要跟她吹的。我没有怎么痛苦就作出了这个决定,这决定好像是从她妈“借簸箕”的时候就开始作了。可是,我没有理由为自己解释。我问我自己:假若你不上学,这决定最终能够作出吗?我不能回答我自己。那么,你不作出这样的决定,将来对她就一定会好吗?我仍然不能回答我自己。
不久就是寒假。
我把我的决定说给了我妈。我妈先是嘴唇颤抖,剧烈地颤抖,然后哭了,不断地用袄襟擦眼泪。我妈说:“没有法跟人家说啊!张不得口。”
我说:“我自己去说。”
我妈说:“你自己去?能叫你有腿进去没有腿出来。”我说:“真玄了!她还敢打?”我这样说着,高高大大的她和高高大大的她妈就在眼前晃动着了。
我到底没有自己去说,我说给了表姐夫。表姐夫先是发火,问我为什么。我说没有感情,没有共同语言。表姐夫冷笑了一阵问我,是不是在学校里另抓了。我说没有。表姐夫说,那么你敢这么大撒手? 要吹也得有个吹法,先抓上一个垫着底再吹。我说,那样最起码得等两年,太坑人了。表姐夫说你以为这样就不坑人啦?这姑娘真也命苦,先前被那个当兵的坑了一回,病了一场,这回又遇上了你!我没有法去对她说,她妈还要你正月去探亲呢,你自己去说吧。我就央求表姐夫,还是你去说吧,最好等我开学走了再去说。我这么说着便发觉,原来我是怕她的。
正月里我去老姑表亲戚家探亲,自行车货座上载个红包袱系住的席篾盒子,盒子里装个滚了好多路的大枣饽饽,装一包跌出了不少面面的桃酥,沿着中流河东岸的大道,向南。天气已经有些暖和了,春天的气息开始在中流河上流动。沿河的冰很薄很亮,河中间的冰已经融化,河水很清亮很轻快地流,看得清河底的亮沙。河边的柳树依然光秃着枝条,仍然没有泛起绿色,只在默默地期待。
就在中流河的上游,东西横拦了一道水库大坝的地方,我忽然看见了她。她走在四五个姑娘中间,她自然高出了一截。她们都是步行,她没有拿什么东西,走得很轻快。这时候太阳正挂在东边的柳树梢上,从侧面向她投撒着灿明的光辉。她蓝色的上衣镀了一层微红的光晕,显得很明丽,甚至有些炫目。她的短发乌亮,柔光,她的脸比往日白嫩,透着健康的红润,她的眼睛亮亮地漾着笑意,向我看着。我这时候才发觉,原来她竟是美的。
“探亲哪?”在伙伴们吃吃咯咯的笑声里,她朗朗地问我。
“啊,你也是?”我已跳下了车子。
然而也并没有多少话,站也没有站下就各自分头走了。她向北,我向南。
这一夜我没有睡好,我的眼前不断地交替浮现着大大的身架大大的手,还有乌亮柔光的短发白嫩红润的脸。在这之前,我没有为她痛苦过和愉快过,思念的痛苦没有,厌恶的痛苦也没有,甜蜜的梦没有,焦躁的失眠也没有。没有这些就等于没有这桩事情,现在有了,可是太晚,不是因为我已经作出了那个决定。
她妈捎信来,叫我去耍耍。
我妈可怜巴巴地看我,我的心被我妈可怜巴巴的神情揪得直抖。我努力硬着心,止住它的抖。
我没有去她家里探亲。
离家回学校的前夜,我将要睡下的时候,表姐夫来了,挟着个包袱,包袱里是我妈通过表姐夫的手送给她的东西,现在送回来了。表姐夫说,她自己送来的。我问什么时候,表姐夫说就是今夜,刚走,就她一个人;留她,她不住。
我愣怔了一霎,转而追问:“她一个人走了?”表姐夫回答:“嗯。”
我即刻拔腿出门,快步向东追去。
夜寒袭人,月光下的山地冷寂而悠远。远远地看到高高大大的身影在月光下移动,我撒腿跑起来。高大的身影愈加快速地移动,我加快了脚步,渐近时低低地喊一声:
“等等。”
她停住了。
我靠上去。
“你想干什么?”旷野里她的声音威严地形成一道防御的大墙。
“我……”我喘息着,说,“我送送你。”
“不用!”她转身走去。
“黑夜,你自己走不行。”我跟上她。
“该你什么事?”
“你听我说……”
“你回去!”
我不,仍跟着她。
“你回不回?”她站住了,盯着我,目光如月光一样冰冷,声音如寒气一样严厉。
我被镇住在月光下。
她又转身走去。
我看着她高大的身影在铺着月光的山道上远去,渐渐地矮下去,小下去,直到看不见了。她去的方向,乌悠山黑黢黢地卧在那里。不知道哪一年,也是在夜里,山腰处烧起过熊熊的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