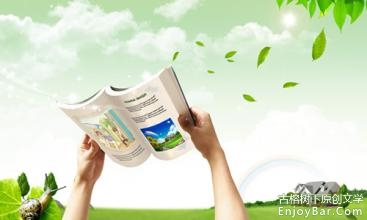王朝明
秋深了,到山里去,访一些老友。
他们一直都在山里。不像我,寻常在山外,偶尔到山里走走。800年,1000年,1600年,这是他们呆在山里的时间刻度,这些刻度镌在他们的身躯里骨子里,我们通常名其曰“年轮”。
他们是一些树,一些很有年纪的树。古树半成仙。山深老树多。崂山高远深邈之处,上了年纪的树是有一些的。有柏,圆柏,侧柏。有槐,国槐,而非舶来的刺槐,也就是音译卡秋的洋槐,刺槐来到岛城的历史不过百余年。有老榆树,榆树就是榆树,榆木疙瘩的榆,没有中外土洋之分。
每棵树都有自己的季节。深秋里,我心心念念想着去拜访的,更有他们。他们是银杏,古银杏。
本草里有一味药,叫金银花。夏天里,去一个荒圮的村落,在残垣断壁上,看见一条青藤,拖着金盏银盏似的黄、白小花,在清清的风里颤颤巍巍,邀醉梧桐树下寥寂的时光。这便是金银花。于是想到了银杏,觉得他们可以被叫作金银树的。不是么?秋来树叶黄了,灿灿的,披着金甲锦鳞一般;黄叶之间还缀着累累的果实,白果,也叫银杏。金的叶,银的果,不就是金银树么。
不过人类看重的所谓名号,所谓财富,于银杏或许并不在意。一棵树,一棵落脚在山野之间的树,头顶有云岚,有高天,有日月星辰;脚下有泉,幽幽的或泠泠的泉,有湮迷的草径,有一方可以把根深深扎进去的土地,而不管这土地是不是贫瘠;身边,则是来去无心的风。
较起市井庭庑,山野中,每一棵树都活出了更多的率性和自由,当然,也承受着更凛冽的风霜。没有一块土地会嫌弃她怀里的草木,即便它再怎么卑微;一样的,再怎么贫瘠、偏僻,树从来不嫌弃脚下的土地——且与大多数的人不同,如果树可以自己选择的话,在野,应是树们心底里的第一且惟一选项。
天下的每一棵树,觉得它们骨子里是在野的,根脉里奔流赓续的,不是对人间烟火滚滚红尘的歆羡,而是对光风霁月高山流水的挚爱,可是,即便是人生一世,不如意者往往十之八九,何况一棵树之一生呢。
好在,造化终究还是厚爱这些树的,因为造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不爱说话,秉性木讷且沉静,有些执拗,认准了的事情,八头牛也拉不回来,肯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拥抱脚下的一块土地,守望头顶的一片天空,做一个长长的循环往复却总也无厌的春秋大梦。
造物让这些树将脚跟立在山野之中,却又不想让其与人间烟火离得太远,于是,就让一座一座的庙宇、宫观、寺庵,做了他们的邻居。没想到,这样的搭配,每每成全了古树与古寺(观)的千年之缘。孰道天地无心造化无情!
所以,寻谒古银杏,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去寺庙宫观。特别是那些深山里的庙宇。古木跟古建的关系,有点儿像唇舌,总是相依相濡的;但或许更像是唇齿或舌齿,当然古建是齿,因为好多庙宇的生命长度,总是不及古木的年轮密度。这也正常。古建的生命是人给的,而古树的生命,也许一开始是人给的,但之后,如果人不是那么多事的话,树完全可以打理好自己。况且古建的根,再怎么挖掘、夯筑,总是不如树扎得深。
在崂山东麓,海拔七八千米的山谷里,有座明道观。最早的基石在唐朝被砌下。与道观一起扎下根来的,还有三棵银杏树,但早先也许不止三棵。风雨,光阴,但更多的是因为兵燹,道观早已圮落,墙垣坍塌,葵谷旅生。银杏树却婆娑依旧,风华也不曾减得半分。
曾经在不同的季节里前往明道观,主要是奔着这三棵古银杏去的。特别是在秋天里。三棵老树,老得让人仰止的树,煌煌昊昊地站着,在邈远的山中,守着一座道观随烟的记忆,也守着其沉寂的当下。
明道观少有人来,除了一些同样痴嗜山野林泉的驴友。深秋,三棵树会迎来其一年里最华彩的时间,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十月底十一月初。当然也不确定。有时,一股急性子的寒流,一阵冷雨,一场凌厉的风,会让银杏披挂金鳞锦裳的时间提前开始,也早早结束。
在树下,腆着脸,微微眯着眼,将心里某些东西放下,又把另外些什么明亮地敞开,这是一个荷杖逶迤而来的行者,在明道观前喜欢做的事情。
没有风。一刹那,时间和老树、圮观都是静止的。天上有个太阳,很大,很空旷地浮在群山和高穹之间,天边有一抹湛蓝的海的影子,有一朵步子慢吞吞的白云,梦一样蹀躞过来,又梦一样蹀躞而去。明道观的前里,有一道山涧,涧底的泉这时也安静下来,幽幽的,在草木的须根和石罅里无声地流。
没有风,叶子也开始飘零。嚓,嚓,叶子在阳光的瀑里坠落,落在树下的荒草里。噗嗒,这又是一枚银杏果。明道观前的两株银杏,一雄一雌,巧合的是还男左女右哩。上年秋天来时,银杏果落得满地都是,石阶上,井池边,空气里流淌着很特别的味儿,清香,或者说还有一点儿微微的苦臭。经验里相反相悖的味的两个极致,却也可以糅合在一枚外金内银的果实里。这里面蕴含着道吗?也许吧。味道吗,有味无味,多味少味,静静品,慢慢嚼,许都能咂出道的回甘来。
左边的树下有块石碑,早已漫漶得辨不出文字了。不过只是立在那儿,就很耐读的了,就像这古银杏。不须靠得太近,远一些望着,在心里摩挲着银杏皴裂斑驳的树皮,还有被蚀曝得光滑平砥的碑面,觉得时间在这里不再是虚无的存在,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质感、骨感,以及温度和重量。
起风了。
这些风们,它们是些长不大的孩子,一百年,一千年,每一个春天,每一个秋天,它们都拉着手来深山里,探望这些银杏。风们哈哈笑着,声气很大,嗓门很高,疯疯癫癫的样子。它们仆仆地赶了很多路,却不觉得累。春天的时候,风带着缥缈的雾岚和濛濛的细雨,灼灼的映山红,还有跟韶光一样清亮的鸟啼,来到银杏身边。它们拽着古银杏的枝桠,把沉沉梦中的老树晃醒了。银杏的心里生出些暖暖的东西,在小雨里,他们的枝桠慢慢伸出青碧的叶子,就像伸出一只只小手。老树的手拍着风的手,发出山泉和阳光的声音。老树和风都很快乐,他们的快乐简单、澄澈,而且明亮。
深深的秋天里,风们又来了。风跑到天边去,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但并没有忘记旧时的路。这番回来,风展示了它们学到的魔法。秋阳是风变魔法的“托”,阳光灿灿的,笑眯眯的,晃得山中草木有些眩晕。只须一两个正午,风在秋阳的帮助下,就会把古银杏满头满身的碧玉和翡翠,悄然抟化成闪闪亮亮的金箔。
风唤醒了深藏于行者心底的童话。童话里也有一株银杏树,那株银杏树孤零零地站在秋天里,脚下是荒草萋萋的原野,天和地都大得没有边际,风从般若世界的外面跑来,仿佛跑了几千年的样子。风一来,银杏树上的黄叶就开始飞舞。天知道这是一株怎样的银杏,他的叶片仿佛从一条银河里泻出来,源源不断,纷纷扬扬,铺天盖地,而银河的另一端却连着时光的黑洞,金闪闪的叶子滚滚向前,黑色的时间却逆向而驰,永不回头。
风把一枚黄叶送到脚下。捡起它,将它迎向午后的阳光。叶子与光合二为一了,那些浩大汹涌的苍凉,在这片小小的灿煦的光里,一瞬间土崩瓦解。那一霎,行者又看到了童话的影子,长长地,拖着一个金色的扫把,在西风呼啸的旷野上踽踽独行。
深秋,古树,叶子静静凋落,世界退到大山之外,置身这样的情境,行者很容易就会陷入自己的心里。那些叶子,每一片都有着清晰的纹路,每一条纹路都知道自己的来路和去处,就像行者脚下走过的那些路,一条,又一条,在尘土、风雨和荒草中悄然消隐、湮灭,却总会在连绵岁月的群山之巅,倔犟地挺起脊昂起头来。
明道观左侧,还有一棵银杏,是雌树。树下有一盘老碾,碾砣和碾盘已经分离,杂草丛生其中。较之观前那两棵银杏,这棵的枝叶一样葳蕤婆娑,果实一样累累,个头却要矮一些。秋风里,他的灿烂时间来得也要早那么几天。
三棵树,站在汤汤的时光里,一站就是一千多年,想想真不容易。不止他们,大地上的每一棵树,跟人一样,谁又能比谁过得更容易些?庄子的《山木》里,一棵树因为不材而终其天年,一只雁却因不鸣而见戮。辛弃疾有所感,于是写下了“材不材间过此生”。但这个材与不材,其实是很难拿捏的。再说了,何必非得去拿捏、算计甚至为此而处心积虑委曲求全呢。想想吧:一棵树憋憋屈屈地活着,来了个砍柴的,就挺挺胸摆出一副栋梁的样子;瞅着个修大船、起高楼、盖宫殿的,就缩缩脖子装成一蓬灌木。累不累呵。
所以啊,不必想那么多。水精灵怪的人算,都还不如天算,何况一棵木木的树呢。交给造化好了,思考不是一棵树必须去做的事儿。天生我材,就按照我材的模样和内里,长就是了,该发芽发芽,该抽枝抽枝,该开花结果就开花结果,该落叶了,即便没有风,也照样落。就像明道观前的这三棵古银杏树。
千百年来,在国人的下意识里,似乎只有那些郁郁不得的士子文人,才会想到归隐江湖,跑到深山老林荒庵古寺来。往往是这样,他们在人堆里受了排挤打压甚至罗织的构陷,百口莫辩:其实能辩亦无须去辩,终归是浪费时间无甚意义。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脸上堆着格式化的笑,傲慢与偏见在笑的褶皱里蹭痒。观点确立了,再去收集论据,盯着一个行者的脚底——看,鸡眼,却视而不见一个坚硬的老茧下,连着多少荆棘丛生曲折颠簸的长路。
那些失意的人来了,却不像一棵树,既来之则安之,则落地生根于斯,一生一世再也不想离开。人毕竟不是树。于是,每每这些迁客骚人,一着纵情山水长啸低吟,一着还放不下舍不得,偷偷拿眼角瞄一下远远的山外,看那条荒杳的小路是不是卷起了尘土,心底里,犹然丝丝绕绕地存着些一骑驰来圣主诏唤的念想。
嗨嗨嗨。在这点上,人终究比不得树。树就无所谓了。而且恰恰相反,人以为的难以释怀,却是树企望的难得自在。在朝,不如在野。大隐、中隐,不如小隐。一棵树的哲学和天地观,根本就跟人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树懒得跟人理论。有那工夫,不如淋淋雨,听听风,晒晒太阳。对一棵树来说,即便在荒山野岭凌霜傲雪,忍受旱魃、荒火、骤雨、白毛风,也不愿厝身于熙熙市井衮衮庑殿之侧,配享金樽玉馔袅袅香烟。
然而这却并非完全由着树的心性的。一棵树,根扎在哪里,有时要问问无聊的风,有时须等待一只贪吃的鸟,更多的时候,人类对树之功用、价值的审美、审丑,常常会令一棵性本爱丘山的树,不得不离开其在野的状态。
以是,明道观前的这三棵银杏树,得以在这山高水远的荒渺之境落脚栖身,穿过千余年的风风雨雨,依然根深叶茂,气象森然,蔚蔚大观,该是何其有幸,又何其难得!
到明道观的路因着高邈迢远,访谒一趟也不容易。当是时,一个踽踽而来的荷杖行者,且好好珍惜这天地之间冥冥修来的缘分,感怀这岁月之河迢迢渡来的际会,默默地,在树下,仰望一片灿灿烂烂的叶子,照亮浑莽大山和平凉心境的这一刹吧,这一刹的光,这一霎的静,这一霎的温暖、安谧和澄宁寂然……
明道观前的三棵树,应该是崂山海拔最高的古银杏了,它们的树龄也着实令人仰止。树干上的铭牌,标注其都在千年以上。从《青岛古树名木志》里看到,崂山千年树龄的银杏树,有十七株之多,而全青岛域内,千年古银杏也总共才23株。造化是偏爱着这一座崂山的哦。
明道观的千年银杏,在古银杏里已经不算年轻的了,可是还有比它们更老的。
在蒲松龄写下《劳山道士》的太清宫,有28株古银杏,其中千年以上树龄的有5株。金秋时节,到太清的游人,好多就是冲着这些闪亮的古银杏来的。三官殿中院的两棵,籍载是公元960年宋太祖敕修太清宫时栽下的,据说由道长刘若拙亲手所植。想来当年的蒲公,也应该常常在它们的影子里斟茶、阅经,听风、纳凉,伫雪看山,也沐浴满天星光守望一轮水月。那《绛雪》和《香玉》的腹稿,也是在银杏树下打好的吧。可惜没有给这些古银杏写点什么。大概,是这些老树身上没有故事,或者,故事太多了,不知道从哪里写起好了也未可知。
上清宫也有两株千年银杏。印象深的是山门外的那一株。它不是一棵树,而是一片树林。母株在中间立着,环绕一周,是它的子子孙孙们,竟有百余株,此中一棵子株达20米,树龄约150年——天,这是它的小小孙辈,竟也令人中之高寿者,难以望其项背了。孰道草木不如人。
去过几次明霞洞。明霞洞是以云岚霞霭为胜的,“明霞散绮”是“崂山十二景”之一。明霞洞有三株古银杏,它们比明道观、太清、上清的千年古树年轻一些,但树龄也在700年以上。洞侧的一块石壁上,有人题下了“天半朱霞”,可以想见飞霞散绮之美。其实,觉得深秋里,银杏叶飘飞的时候,更是“明霞散绮”之一种,不过此时散的不是朱霞、紫霞,不是红绮、绿绮,而是灿灿的金霞、黄绮。披上这金光闪闪的绮罗,不惟明霞洞,整座浑莽的崂山都亮了。
白云洞,远在白云生处的崂山东麓,雕龙嘴村西的冒岭山之阳。一雄一雌两株银杏扎根在这里,一起阅尽千年白云,走过了婆娑的春秋和风雨。白云,青天,沧海,大山,这是两棵树视野里最寻常的事物,并且它们也希望这样平淡而悠远的光阴静静地迁度下去。然而怎么会呢?造化不惟不仁,有时是多么的无情。1939年的春天,农历三月十五,光天化日,东海崂山山水水生机勃发,两株正在萌叶的古银杏,满以为又将迎来一个郁郁葱葱的生命轮回,孰料,他们却亲眼目睹了6个鲜活的生命,牺牲在侵略者的炮火和屠刀下。山河破碎,沧海呜咽,生灵涂炭,那一刻,两株古银杏的血脉该是如何的偾张。
81年后的早春,我去访谒了白云洞。草木无声,天地无声,那一天,在荒圮的白云洞,远来的访客除了我,只有白云和风。两株古银杏已满树青翠,碧玉的小扇子在韶光和东风里微微颤动。可是我看到其中的一株(大概是雌树)树冠和半个主干业已斫去,只剩了一人多高的树桩,这棵银杏应该是枯死了,跟以“云洞蟠松”蜚声的那棵华盖古松一样,但好在从银杏根周,又蘖生出了子株,尽管纤瘦,但新生命的力量却是倔强和蓬勃的,在浩浩汤汤的流光里,又一个千年之旅已经开启。
也是在崂山东麓,华严寺有三株古银杏,一株在寺门外侧,两株分立在塔院外的路边。印象里,华严寺银杏叶子应该比明道观黄得要晚,这主要是海拔的关系。寺门外侧的那棵银杏,叶子流金的时候,衬着山门上的匾额和两侧的对联,很入画的,也很有意味。有趣的是,山门里,正对着门廊的照壁上,是一尊弥勒佛的浮雕。佛袒胸露乳,无论是黄叶飘飞还是碧玉簪枝,什么时候去,他都笑得很开怀。人间的事情,在弥勒眼里,大抵和银杏树的叶子差不多的,任是色相、分量,还有泯归尘土的那一笺虚静空灵之音。
蔚竹庵,这座深藏崂山深处北九水的道观,如水的光阴,沐着两株古银杏。800岁的那一棵,就在小石桥前。每年深秋时节,这株银杏树下都会聚来一拨拨的游客和驴友。琳琅的金叶飘在空中,落在头上,铺满脚下,那些忘情的人将落叶一遍又一遍地抛洒向空中,为的是将这一霎的“亮了”炫进自己的朋友圈。呵呵。此时,古银杏身上发散着慈祥的光,它默默地伫立着,配合膝下这些垂髫或白了头的孩子们,将自己的影像镌进他们的心灵,照亮他们的人生旅程。
有年深秋,十月,记得是农历十月初一,那么早,崂山的第一场雪就来了。荷杖分荆,我一个人在山中走,路过蔚竹庵。古银杏叶子已开始变黄,可是还未完全换成金裳,还有些青碧的底色和边纹。于是眼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白茫茫地,雪在飘飞,一株卓荦轩昂的古树,披着金碧辉煌的大氅,在翠竹丛中,在恢弘浑莽的大山里,凛凛而立。有些风,但不是很大。有竹声,也不是很大。雪里的一切,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和默片一样,让人恍惚忘记了时间,恍惚忘记了去路和归程。
华楼宫在崂山的“龙尾”上。觉得在这里,东海崂的形胜得到了形的定盘、神的游骋、意的澄静和气的捭阖。定盘的是一石,华楼叠石。游骋的是二水,天落水,月子口水库。澄静的,是这座道宫和它观照的这方天地。捭阖的,是浩浩汤汤的光阴与无际无涯的六合。而五株古银杏,则是道的承载,载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道、四季轮回的天地自然之道、随遇随缘乐天达命的立身处世之道。去过几次华楼,在不同的季节,每次去,在银杏树下站站,或远远地望一望,心性就像叠石、像天落水、像崂山水库一样,定了,澹了,静了。就像那一片片明灿灿的银杏叶子,任是有风无风,无论留在枝头、飘向空中还是落在地上,都是一样的安然和从容。
崂山西麓法海寺内,有两株古银杏,一株1600多岁了,另一株也逾千年。有年冬天,经源头村去华楼山白鹤峪看天落水冰瀑,途中过法海寺,就进寺访谒。法海寺据说是青岛域内最古老的寺庙,虽不在深山,挨着市井,置身烟火红尘,却很安静。彼时天寒地冻,银杏树叶早已落尽。在树下仰望,苍灰色的树干,皴峻,粗壮,擎天柱一样,撑着虬枝,巍然屹立。可以想见,如果来的时候是秋天,风叶成金,古银杏应该是披着黄色袈裟的高僧的样子吧。
草木与青山,在彼此的眼里心里都是妩媚的。名山抱古木,古木也爱偎着大山。如今,在山脚下的村落里,在山中寺庙道观里,几乎崂山的每一个角落,都能谒见到苍苍的古银杏。不过遗憾的是,在崂顶,在巨峰的附近,却没发现一株。也许以前有吧,因为在巨峰南麓,有玉清宫还有铁瓦殿的遗址,不过都坍圮了。铁瓦殿据说是遭过火烛之劫,那么即便当时有古树在,也大概与瓦殿一起羽化了。
遗憾是有的,不过转念一想:古银杏也不是天生的古银杏,千岁翁也是从小时候,从小不点儿一天一天长大的。起初小小的纤瘦的银杏们,将根扎在崂山的山山水水,一晃百年,一晃千年,慢慢就把自己变成了根深枝繁的古银杏。感慨过往,不如珍重当下,就是现在,也可以在巨峰栽植些银杏树的。这样再过百年、千年,后人就可以在崂山的最高处,访谒令他们仰望和惊叹的古银杏了。一如眼下的我们。
大地上的每一个村落,都是喜欢与草木相依为命的。这喜欢是骨子里的喜欢,打心眼里。比如,它会默许甚至纵容一棵树将自己长进院墙里,任那些草籽在屋顶、墙头、瓦隙里扎下根来。村子还打心眼里喜欢上了年纪的树。如果一个小村子里,能有一株千年老树,那么这个村子真是幸运。崂山脚下的王哥庄有几个这样幸运的村庄。一个是东台村,它的怀抱里有一株国槐,据说是在唐朝时种下的,如今依旧生意盎然,气象蓊郁,花开时节,青蕊如海。另一个是囤山前。村子里也有一位千岁翁,是银杏。古银杏年纪很大了,可是童心未泯,它不仅天天呆在幼儿园里,跟孩子们在一起,还喜欢玩捉迷藏。呶,竟然把自己三大主干中的一枝,藏进了墙里,然后穿墙而过,这不免让崂山道士自叹弗如。
离东台和囤山前不远,有座凝真观,那里也有几株古银杏。一年里,几次去东台看那棵名字叫“槐庆德”的唐槐,却不知,一次次与几棵同样有着大把年纪的古银杏擦肩而过。又一个秋天到来了,古槐和银杏也都将迎来它们灿灿烂烂、亮亮堂堂的时间。那么此后的秋天里,我的崂山村落之行,又将增添新的老友。
于是就去了一趟。与囤山前一路之隔,庙石村里,我访谒了那几株古银杏。据《青岛古树名木志》载:凝真观有4株银杏,两株700余岁,两株600余岁。可我此番去只看到了三株,一株在路南,挨着村民宅院,树干铭牌上标注树龄为1000年;一株在路北,翠竹掩映的小园里,是棵雌树,因着山下海拔低平的缘故,都十月末了,叶子的基底还是碧绿的,金色的银杏果却已熟了,噗哒噗哒,幽然落在地上。这番来谒,正是傍晚时分,那么多的鸟在啼鸣,喜鹊,麻雀,还有叫不出名字的什么鸟儿。这么几棵古树巍巍立着,合着周边十里八村的鸟儿都有福了。还有一株,在更深的观院里,我不知它的树龄多大,隔着院门望过去,与两株千年银杏一样的高拔苍翠,想来年纪也该差不多的。都是很老很老的老头儿,都是老寿星。
崂山最年长的银杏,连着一位渡海而来的高僧。高僧是法显,东晋平阳郡人,取经求法路上的先行者。泛海归来,登陆长广,据说上岸地就在崂山的栲栳岛。然后一座石佛寺(后来又叫潮海院)立起在崂山海边,一起立在浩荡海风中的,还有几株银杏。后来,佛寺隐入时光深处,旧址上有了新建,银杏树却还在,其中最早栽下的两株,如今已经1600多岁了。
够老的了吧。可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我和同事走近,并在潮海院门外远远地仰望,它们却一点儿也没有给我们老迈的感觉。矍铄,从容,很像身边的一种人,就是历尽沧桑却不见颓唐萎顿的那种。不卑不亢地站在那儿,管你寒暑春秋,任你风任你雨,一股子苍虬遒劲之气韵,一袭轩昂的气宇,一树煌煌杲杲的气象,这是潮海院里的古银杏穿越千年的秉持和抱一。
印象里,天下的银杏树都是这般模样这般气质的,即便是仄身闹市街衢一角,被当作道旁绿化树一排排密植下的。谁见过它们中的哪一位,像一棵别的什么树那样婀娜地俯下身去。遑论深山古寺里,这些洞悉了人间炎凉悲欢烟火红尘的,银杏中的苍苍长者。
睹一叶落而悲天下秋,世上的事情有时就这么有意思:春秋迁换,花叶凋零,于人间草木来说,是寻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对于本应是旁观者、局外客的一些人来说,却是其兴发吟赋悲伤怅廓的肇起之因。这些人如果能把一个下午或者午后的时间,放在一株山中古银杏的身边,或许他们会发现,他们以为的草木伤秋之情,原本只是他们自己以为的。
是的,置身古银杏下,一株老树的叶子在头顶幽然飘落,银杏果和风的气息簇拥在身边,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枚白果的凋落都是从容、平静,或者更恰切地说是安详的。悲伤和喜悦,从来都是专属于人的,它们不是秋天的,更不是银杏的。摆脱悲伤和忧怅,趋鹜欢喜和快乐,一株古银杏没有这样的向光性。
每一缕光风每一场霜雪都对应着一道年轮,偶尔圆润,寻常嵖岈。不必怨艾什么,冷也好暖也好,既然身为一棵树,不惟阳光雨露,疾风、高霜、沃雪,斧钺、爨火、兵燹,都是可以预见的际会,也都是必将直面的宿命。对一棵有着上千年阅历的老树,更是如此。
行走在深广宽厚的大山里,山路之上时有风雨阴晴,却都无碍脚步、心灵与草木山川的应求与共鸣。有时,不为别的,就专为去看一看那一棵棵动辄千年之龄的古银杏,而将半日浮生掷于山中了。
有人说,有些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大山里的银杏,没有一棵会作如是想,怎么会是浪费呢——拉住那总是在埋头赶路的时间,将它留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这是多么的物尽其用呵。
而且,这个世界上,总还有一些人,跟银杏一样,也喜欢把心灵的脉络和时间的根须,深深地,静静地,扎进亿万年来未曾有过丝毫改变的山高水长中去。
深秋里,向老树,向照亮大山的那些老树学习。
并且此致,敬礼,还有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