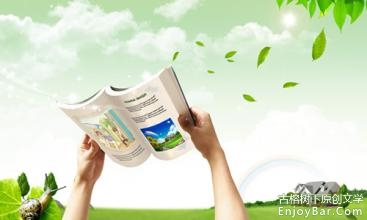李 晋
花 菜
徐州朋友说的“菜花”,我初以为是春天遍野的油菜花,后来方知道是我爱吃的“花菜”。“菜花”之名偏于尝食,“花菜”之名偏于欣赏,我地和徐州同处一省,但对同一蔬菜叫法却有区别,这是值得研究的话题。花菜本生长于地中海东岸,19世纪中叶,差不多是数万中国劳工前往美洲“淘金”的时候,花菜来到中国,先是在沿海地区落户,后遍植各地,从副热带夏干气候到亚热带气候,天气、水土都有了变化,但花菜还是和大洋彼岸的中国劳工一样,很好地在异国他乡安定了下来。
花菜的形态,仿若一只充满力量的拳击手套,它的“花”很坚硬,呈粉白色,无柔媚之态,无芬芳之味。如果非要认为它是“花”的话,它就好比是穿上戎装、始终没有退伍迹象的花木兰,看上去比男儿还甚,充满铁骨铮铮的风度。“铁骨”一词形容梅花较多,我知道一位号称“梅花王”的画家,他就喜欢在画作旁题上“铁骨梅花”的款字,但画的梅花总柔弱的比小乔还要小乔,这般姿态,自然要让我小瞧。
“花”是花菜的主要食用部分,可以不用菜刀,把它的“花朵”一块一块地掰下来入菜,最后剩下来的花菜根梗,像是寒风洗礼后的矮树,仅根部残留着三两片没精打采的绿叶,这“矮树”主干粗壮,肉质坚硬,故家庭不会拿来做菜,有一次,我吃到了一道味道有点接近酸笋的凉菜,一问,才知道主料是花菜根梗,这是几乎没有成本的菜肴。
分散成若干小“花”的花菜要先用盐水泡,泡掉“花”内的细缝里的虫子和其他杂质。虫子寄居其内,看似讨嫌,实则表明花菜“绿色”成色之足。泡后的花菜还需用水焯,热水减去了花菜的苦涩,软化了花菜的质地。这两个步骤属于前期的功课,要是省略,难免失了营养,少了滋味。烹饪如同打拼事业,细节决定成败。
荤烧比素烧的花菜好吃,荤烧多配肉片,但我地多数饭店的菜单上,肉片成了“无名英雄”,往往这道菜叫做“手撕花菜”或“干锅花菜”,“手撕”取自择菜方法;“干锅”是根据烹饪手法定名,花菜、肉片炒至八成熟,放在下面置放酒精炉的小铁锅内,锅炉一起上桌。蓝色的火苗在锅底蹿动,锅内菜肴的汤汁逐渐耗干,“干锅”一名缓缓到来。看来饮食的乐趣重在过程,吃在嘴里的,有食材的前世风采,有食材由生涩到成熟的蜕变。
现在还记得幼时,家门口临河的菜市场,有农人运着近乎一船的花菜在河边售卖的场景。那花菜个头很大,饱满且紧致,与现在标榜“有机”的青梗松花菜有很大不同。
萝卜丝包
萝卜丝包子和肉包、青菜包是苏中地区茶馆里的常规点心,一年四季都有。以身价论,肉包是老大,萝卜丝包和青菜包是孪生兄弟。我平日里常吃到青菜,因此我是选肉包或萝卜丝包居多,一般点上一只,佐干丝或面条吃。看外观,萝卜丝包和“老大”的行头更接近。虽说包子的面皮是一样的,但青菜包的馅心绿得鲜明,面皮包藏不住这一腔春意。萝卜丝包和肉包则容易混淆,它们表层面皮上的油斑很相似,油亮、泛着乳黄色,有雨天后的通透之感。以前我在想吃肉包、偏偏又囊中羞涩的时候,总寄希望发放面点的师傅能把我点的萝卜丝包错拿成肉包,可是我一次也没遇到这样的情况,后来我发现了端倪,原来肉包和萝卜丝包顶上收口处是有区分的,肉包收口松,萝卜丝包收口紧。
往小处说,这是暗记;往大处讲,这是风格。做包子需要这样的设计,做人也需要这样的个性,千人一面的世界,实在无聊乏味。
每家茶馆做的萝卜丝包(当然其他包子也一样)味道各有千秋,馅料的主要食材虽然都是萝卜丝,辅料却各自不同。有的喜欢加肉末,有的喜欢配香菇丁,有的喜欢放青蒜,有的喜欢什么都放一些,搞得像是什锦包。合我口味的一家茶馆所做的萝卜丝包,里面是细细的萝卜丝、木耳末、香葱花,辅料也仅盐油而已。不沾荤腥的包子清清爽爽,作为佛家的素斋也并非不可。
蒸笼里的萝卜丝包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咬开后的萝卜丝包香味直窜,手在包子下方一捏,会有油汁涌现而出,依附在咬口处的一根根萝卜丝上,再把泛着光亮的萝卜丝馅连同面皮咬入嘴中,绵滑、柔韧席卷舌面,嚼至末尾,又有单刀直入的脆嫩,和口水“会师”后的油汁,仿若净化成水,味觉湿润如热带雨林,概因是萝卜有吸油去腻的功能。
能体现萝卜这一功能的还有一则民间故事,说是清代名医叶天士看到一店铺老板天天买肉吃,觉得这样吃日后定会生病,就暗中把喝茶剩下的茶叶晒干了贮藏,准备以后给老板治疗时配药用,结果过了好久,老板也没生病,叶天士很奇怪,后来了解到老板天天吃的是萝卜烧肉,这才恍然大悟。
故事是我幼时听祖母讲的,当时她为劝导我不挑食出此良策。祖母生前很喜欢吃萝卜,也爱吃萝卜丝包。现在我也经常买萝卜丝包给儿子吃,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这是我家具有精神价值的“传家宝”。
三鲜熬面
做人要面面俱到,按我理解,这当中讲的既是脸面情面,也是饭桌上的面条。我虽不是顿顿吃面,但也是经常吃面条,有时吃汤面,有时吃拌面,有时吃炒面,有时吃焗面,偶尔会吃熬面。吃熬面的时候,我想到“媳妇熬成婆”这个俗语,面容姣好的少妇,恍惚间已成满脸沟壑的老太婆。我不喜欢“熬”出现在岁月中,它磨掉了时光的情趣,轻视了生命的价值。我喜欢饮食中的“熬”(当然熬药除外),它是一个向美好过渡的过程,去粗取精后,映入眼里的是美妙,落到嘴里的是美味。烹饪和品食连接在一起,才是值得享受的完整美食。
熬粥熬去的是水,熬面熬去的是汤。煮透的面条,捞至开水中过一下,置入汤中熬煮。汤是预先备好的,光鸡、鸡爪、猪手汆后,配上葱姜,搁锅里,倒入清水,放煤炉上,盖锅盖,煮沸腾后,再转小火焖煮,中间换四五只煤球,当末代煤球逐渐由黑转白,炉火就打起瞌睡,直至完全熄火打烊。此刻揭开锅盖,食材变得烂熟,也变得若有若无,乳白的汤色挡住了它们伟岸的身姿。
以这浓汤再熬煮面条,加些笋片、木耳、肴肉、河虾,最后再放上烫熟的小青菜,撒上虾籽,添点盐和胡椒,就是三鲜熬面。鲜的滋味在食物里,在幸福中,我看他人低头吃熬面的情形,热气缓缓飘散,肉眼观察到的,不仅是热火朝天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的人间。
三鲜熬面的鲜美,靠的是慢功夫,功夫慢,不代表行动慢,以前我想吃熬面了,和母亲说一下,我立说,她立行,准备好主料辅材,两三个小时后,一碗三鲜熬面就端到我眼前。某日,我看到母亲头上白发突然多了不少,就在饮食上没有再提什么要求,想吃什么,或自己做,或是买现成的,不给老人添麻烦,是尽孝,也是尽善。
市面上供应三鲜熬面的小吃店很多,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熬”功不够,汤不入面味,观之尚可,终究是表面文章,耐不住琢磨;有的汤有“水分”,甚至骨粉炖汤,鲜的舌尖泛麻,食后口干舌燥;有的偷工减料,如以火腿肠代替肴肉,吃在嘴里像是吃的塑胶片,这么说并非全盘否定火腿肠,只是说它出现在熬面里终是差强人意。好的食物,讲究食材合理搭配,就像用牛奶泡油条,中西混搭始终觉得别扭,远不如豆浆泡油条更有滋味。
吃三鲜熬面,食面条、尝配菜、喝浓汤,仿佛依次走入了鲜意三境界。这与国学大师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学习三境界有同工之妙。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同样,治大学若烹小鲜。
锦绣南瓜
东(冬)瓜西瓜南瓜北瓜,看似四种瓜,实际只是三种瓜——北瓜也是南瓜,这是皖苏部分地区的叫法。身兼两职的南瓜相当于又打工又务农的勤劳汉子,当然也可以形容为南北吃得开的商界达人。南瓜有圆形、长形两类,圆形肉质紧密,长形肉质松散,把两种瓜放在一起,特征如金庸《鹿鼎记》中的瘦头陀、胖头陀。有胖才会瘦,有瘦才会胖,这是人类。南瓜长圆胖瘦天生定,所以做人更要变通。
我喜圆南瓜胜于长南瓜,我爱橘色南瓜盖过青色南瓜。圆南瓜有福相,橘色南瓜有喜色,综合一处,我所喜爱的就是橘色的圆南瓜,这样的南瓜饱满圆润,外表清爽,打开它的内心,是一片金亮,我给它定名为“锦绣南瓜”,念叨着这个名字,我便想起友人锦南,她面如满月,眉清目秀,举止投足间尽显温婉端庄,是一位有灵性的女子。
南瓜的温柔气息,还在于它的甜,切成小片,熬粥时放入,高温促发南瓜化肉为泥,融进粥中,粥面遂有了金色的光辉,米粒骨子里是不想被同化的,这样的纠结让它呈现出奶黄之色。粥里面生出了一些甜味,甜得不发嗲,甜得很妥帖。要是熬粥所用的是小米,就是“双黄粥”了,其可与双黄蛋搭配,却不可与炒作过头的双黄连口服液佐餐,药食同宗同源,但非同时进口之物。
粮食凭票供应的年代,南瓜粥好像是网红电影的主题曲;现在南瓜粥和南瓜饼归于点心小吃,变成了冷门电视剧的片尾曲。有时候我连这“片尾曲”也省略了,直接把南瓜切成大块小块,和山芋一起蒸,饭熟了,瓜芋也熟了,在物质丰裕的今天,这样的吃法简单粗暴,仿佛就是无从配曲的三流诗作,成为歌词没有可能,但勉勉强强可以称为打油诗,围着柴米油盐转换的老百姓却需要这样的“打油诗”。
乡人把个头大的南瓜称作番瓜,家乡有一地名叫“番瓜嘴”,我听老人讲过这个地名故事,某年发大水,一人靠攀爬上一棵大树,才未被洪流冲走,他栖身树上,饥饿难耐,也许命不该绝,突然间,他看到水面上有个瓜嘴蒂,捞上来一看,竟是一只圆滚滚的老南瓜,凭借这只南瓜,他生存了下来,水退后,他怀揣感恩之心,把这地方叫做“番瓜嘴”。
这样的传说,让我对南瓜刮目相看,它是瓜,是菜,是饭,是救命的粮食。
南瓜自己会救自己的命,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一些南瓜,表层有疙瘩疤痕,有的形状、纹路还与器物景象相似,这是它疗伤的印迹,当瓜皮被虫子咬后,它便分泌一种液体,保护自己的伤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对南瓜而言,是一种磨难。
在西方的万圣节时,人们会掏空南瓜的瓜瓤,在南瓜上雕刻鬼怪等图案,瓜内放蜡烛,做成南瓜灯。南瓜灯成为西方万圣节的标志,如同中国元宵节的灯笼,这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体现。
参鱼随谈
郊外,有老者在河边垂钓,我上前看其“战果”,脚下桶内,有两三尾参鱼在水中游动,老者转过头来看着我,叹声道:“运气不好,全是小参鱼”。我安慰他说:“参鱼搭酒呱呱叫”。他听了,笑了笑,继续关注起河面。我只有闲时才吃参鱼,因为参鱼刺多,需静心慢品。说起多刺的鱼,最为著名的当属鲥鱼,张爱玲说过人生三大恨事,“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实则不应有恨,换个角度看,事因不完美才有悬念,才产生趣味,才吊人胃口,在我看来,鲥鱼参鱼之刺,是京剧演员的行头,少了它,滋味效果也就淡了。
鲦鱼,是参鱼的学名,它大概学武不学文,形如柳叶的身上银白似雪,看上去似乎就是柳叶飞刀,我更愿意把它叫做小李飞刀——古龙笔下虚构的暗器。说实话,这么想是存了私心的,在下姓李,所以希望姓氏能跟在后面沾沾光。
多数参鱼长度不超过一根筷子,宽度和成人拇指仿佛,它有近亲白条鱼,外观和它相仿,但体形却是它的几倍,价格更远超于它。参鱼的纤小身段,会让吃客有参鱼刺比白条鱼刺多的错觉。在参鱼的肉中,隐藏着一种丫字形的软刺,如树枝改制的衣叉,衣叉是叉下衣服穿在身上,食参鱼是取出叉刺送到嘴里,一收一放,呈现生活多样化。
参鱼食性较杂,夏天的时候,在很多河泊中常能观察到成群活动的参鱼,它们在浅水处游动嬉戏,这时要是扔一小把馒头渣,它们会蜂拥上前,争抢食物,搅动着水面发出轻微的哗哗声响,全然不顾岸边打量着它们的人类。
对于傲慢的参鱼,人们有时会用特制的参鱼网对付它们,这种网由橡胶浮子、铅坠、综丝网组成,网分三层,参鱼进网后,就会“粘”在上面。落网的参鱼当中经常会夹杂着小鲫鱼、鳑鲏等其他鱼类,在专业的渔具面前,“杂牌军”的战斗力不堪一击。
参鱼价贱,加之难打理,饭馆很少拿来入菜。倒是家庭的巧妇喜做油炸参鱼、红烧参鱼。经典的是咸菜烧参鱼,两指紧掐住参鱼,抠出鱼鳃,刮去鱼鳞,开膛取内脏(这是细活,弄不好鱼胆破了,吃起来有苦味)后,搭上葱姜入油锅,再放两把切段的长梗白腌菜,一捧花生米,舀两勺酱油,撒少许白糖红烧,烧熟后,夹一条参鱼剔骨,取细白的鱼肉蘸红汤吃,鲜嫩咸香,有隐约的回甜。把咸菜烧参鱼放入冰箱,稍后取出,挖一块琥珀色的鱼冻含在口中,热气进逼鱼冻,融化的汤汁涌入口中,鱼香奔袭而来,嘴中无鱼,味中有鱼,度化也是烹饪中的一大高招。
我收藏有一张“江淮画鱼人”潘觐缋所绘参鱼册页,参鱼以浓淡墨绘制,颇为生动,但写意成分大于他笔下半工半写的金鱼,韵味各有不同。
芋到好缘
菜上齐后,服务员又给我们端来一只砂锅,里面是散发热香气的芋头片。说是店庆活动,消费三百元赠送的芋头煲。夹了一块芋头片,入口慢品,香软可口,化整为零后,粉糯的小粒分散在舌面周围,像是给舌挠痒,美食之中蕴含情趣。洗芋头就不是乐事了,黑褐色的表皮易粘在手上,奇痒无比,这种痒就有些讨嫌,痒得人手足无措,内心烦躁。小时候祖母让我帮着洗芋头,我洗得愁眉苦脸,这时,祖母会说,洗芋,就是喜相遇啊,这是多美好的事,你看,芋头正对你笑呢。”我当然没看到芋头的笑容,却由此感受到了祖母的乐观。
祖母喜用芋头和五花肉红烧,烧热的油锅里,扔几块冰糖,等冰糖熔化,颜色泛红后,放入煮至七八成熟的肉块,加两勺老抽、小半勺料酒翻炒,接着注进清水,放各式调料辅材慢炖,再加入芋头,收汤出锅。此时的芋头浓油赤酱,软糯香黏,咸甜可口。
这样的好味荡漾在唇齿间,飘在岁月深处。恍惚间,祖母已去世二十多年了,我也到中年,记忆的味道让人挂念,让人着迷,这味道的成分里有亲情味、人情味。
芋头曾给我迷惑,我曾把生活在野外的它误作滴水观音,把室内的滴水观音当它,两者的叶片、长茎很相似。仔细对比后才知道,芋头叶片中心没有紫点,而滴水观音是有的,这紫点仿若观音眉心间的吉祥痣。如此,便容易区分了。
苏东坡说:“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这是形容江南小个头的芋头。芋头品种很多,光吾乡就盛产龙香芋、香荷芋、紫荷芋、香沙芋,四种芋头种植环境不同,各有特色,它们的名字风雅,似乎是从唐诗宋词集子上跳下来的字符,给它们命名的劳动人民充满智慧。
在外闯荡的那几年,我经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太累了不想再忙晚饭,就把买来的芋头、山芋洗净了上锅蒸,去皮蘸白糖食用,吃这样的简餐,让人更会想家。在休息的时候,我会用芋头炖排骨,芋头熟得快,先捞上来吃,吃完后再放,反复两三次后,汤色泛白,排骨也已烂熟,这时撒上葱花,放点盐,喝汤嚼肉,暖意盈怀。
到了过年时,乡人的餐桌上几乎都有芋头,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说是吃上芋头,来年就会遇到好人,所以爱吃不爱吃的大人小孩都会吃上几口,不为别的,只图人生当中碰到更多的良师益友。
芋到,是好口福;遇到,是好缘分。
香菜香
切成小段的香菜,放盘子里,撒一把油炸花生米,搁一些豆干丝,放酱汁、麻油,来回拌几下,就成了“三合一”,这是近年来饭店流行的下酒小菜。“课后练习”版块,可包括知识练习题、英语语言知识、技能练习题和综合练习题。微信公众平台可对学生的这些练习进行追踪,教师可根据微信公众平台的提供的数据对学生的作答进行归纳,了解学生的不足,以加强课堂教学。
香菜之味,醇厚而霸道,在“三合一”中占据核心。它在饮食男女心中,矛盾体般的存在,喜欢者深爱之,讨厌者难以接受,甚至还成立了“世界反香菜联盟”,其使我想到已故画家朱新建的美人图,喜者说其笔墨朴拙浑厚,厌者说其低俗趣味,两极分化明显,但不可忽视朱新建的个性风格与存世价值,有争议的东西才能长久存在。
闻香识女人,香菜的香让我想到东瀛著名女明星花泽香菜,这位长相甜美的姑娘,近年来也经常在中国做活动,比如她有一次在某网站以“我吃我自己”为主题进行直播,视频中,她做了一道香菜沙拉,随后将之食用,并不停地说好吃。上演了香菜切香菜、香菜吃香菜、香菜夸香菜的有趣过程。
明星遥不可及,但香菜触手可得,即便有人不喜,但菜市场断然不会没有香菜的身影,饮食中,的确有很多需要它的地方,陕人拌凉皮、川人吃火锅、江南人下阳春面,少不得它的辅佐,而用香菜和肉末作馅所包的饺子,是北方人喜欢的美食,纵然南北有别,然南北却能在食材应用上寻求到共鸣,饮食看似自成特色,实则存在相互间的联系。
“相彼芫荽,化胡携来。”这是明屠本畯《蒝荽》诗里的句子。句中的“芫荽”,是香菜的另一别名,在本地方言中,香菜被唤作“延须”,幼时,还有一大人和我戏言,多吃香菜能够长胡子,长了胡子就成大人了,我信以为真,央求家人隔三岔五买“延须”做菜给我吃,吃了多时后,我才明白这纯属无稽之谈。
香菜传入中土较早,普遍的说法是公元前119年,由张骞从西域引进,能在神州生根,说明它的适应能力强,虽然看上去它青绿娇弱,茎细如麻绳,叶小如硬币,掐下一点,香气直冲鼻息,这点小伤对它而言,似乎无关痛痒,过几天再看,眼前仍是青绿,凑上前去一闻,香气不消半分。
种香菜能种出故事,北宋僧人文莹《湘山野录》记载一事,处士李退夫在自家菜园子种香菜时,按当地风俗,播种时需口念“荤段子”,这样香菜才会长得好。李退夫是个读书人,秽语难以出口,于是,一边播种,一边默念“夫妇之道,人伦之性”等话语,这时,突有客来访,李退夫让儿子继续完成手头的工作,其子更老实,在撒着剩余种子的同时说,“家父已把该说的说过了”。后据此以“撒园荽”代指文人间讲“荤段子”。
晚年的周作人作有《八十自笑诗》,诗中有“谐谈犹喜撒胡荽”之句,在“撒胡荽”后,周作人自注:“近译路吉阿诺斯对话,多讽刺诙谐之作,出语不端谨,古称撒园荽。”他在翻译古希腊《卢奇安对话集》时,想到了这个典故。我想写完诗的老才子,那一刻必是心旌摇曳,满面春风。这样知情知性、风流入骨的人物,到底也是旷世奇才。
豆 芽
上小学时,有一同学个矮体瘦,大家叫他“豆芽菜”。数月前,同学聚会,我见他已是个高体壮,让我吃惊不小,岁月真是个魔术师,改变了一个人的形象。此般拟人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放在古代,古人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在他们眼里,豆芽很美,这无可非议,古代绝少有化学添加剂,天蓝水清地净,发的豆芽自然好。明人陈嶷专门写过《豆芽菜赋》,他在里面形容豆芽“冰肌玉质”“宛讶白龙之须,仿佛春蚕之蛰”。这一篇美文,是陈嶷科举时所作,他凭借此文一举夺魁,官拜浙江道御史。
在《豆芽菜赋》中,陈嶷还提到豆芽“物美而价轻”,是明代亲民的食材。而在南宋,豆芽给人们带来的却不仅是口舌之美,而是赏心悦目之美,时人陈元靓《岁时广记》载,“以水渍绿豆或豌豆,日一二回易水,芽渐长,至五六寸许,其苗能自立,则置小盆中,至乞巧,可长尺许,谓之生花盆儿。”
在古代,豆芽之豆,最初来自黑豆,这是东汉《神农本草经》上记载的,这亦佐证了豆芽的悠久历史。现今的豆芽之豆,以绿豆和黄豆为主。发豆芽不难,以前我外婆在世时就经常在家发豆芽,面盆里衬一层布,放入浸泡后的豆子,再盖上一层布,使之不见光,接着浇上水,每天早晚换水,五天左右豆子就变身豆芽了。外婆经常所做的是豆芽炒韭菜,条条白丝堆叠在草丛中,周边点缀着红椒丝,盘中一派春光,顺带着香气,夹食一筷到嘴里,又是脆生生的劲爽之感。
在家发豆芽的,不止我外婆,老作家刘庆邦在散文《豆芽说,要创造生活》写了用故乡的黄豆发豆芽的事情,他写道:“我宁可不吃,也不愿到市场上买黄豆芽儿。只有我用老家的黄豆和清水生出的豆芽儿,吃起来才有豆芽儿味儿,才有家乡味儿,心里才踏实。”刘老坚持不吃市面的豆芽,犹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这是游子对故乡精神层面的坚守。
按我个人喜好,我偏爱于绿豆芽,相较于黄豆芽,其更为纤嫩,豆腥味也淡些。绿豆芽适合单炒,也适合做辅菜,比如水煮肉片,就可用绿豆芽陪衬,能消解油腻。近来在一高档食府看到“熘银条”的菜,不解,点菜后,方知是绿豆芽去除须根和顶部两片子叶,留中间白茎清炒而成,因其菜名大有诗意,故菜价大有水分。
藕心菜
我在江南多次吃过藕心菜。现如今物流的发达,让藕心菜也能来到江北我的身边,江南的风光也随着跃现于眼前。江南好,1200多年前的白居易已在诗中表述过。江南有美景美人美食,藕心菜白亮光洁,如养眼的美景;藕心菜清新娇嫩,似赏心的美人;藕心菜鲜脆爽口,是可口的美食。藕心菜浓缩了江南的气质。
藕心菜并不为江南独享,有莲藕的地方,就有藕心菜,藕心菜是莲藕发芽后初生的根茎,故有人认为吃它是暴殄天物,这也造成了它不太为人熟知。某次,我和一外地朋友提到“藕心菜”,他不解其意,以为我所言是“恶心菜”,认为我有挑食的毛病。
在反季节蔬菜大行其道的今天,“不时不食”似乎已成空谈,而藕心菜却固守着自己的矜持,它萌发于夏季,属于有机无公害水蔬,它低调地在淤泥中生长,出水洗净后,便露出白里泛黄的肤色,它整体是修长的,细如小指,大多一些弯度,一侧带有尖头,如武林高手使用多次、有些变形的毛笔。掰开后,会发现它内里也有和藕一样的圆孔,藕心菜可算是乳猪版的莲藕。因之藕心菜有别名藕带,故还可称作荷塘版的海带。
藕心菜做法很多,最普遍的是清炒,切成小段的藕心菜,拌以青红椒丝清炒。炒藕心菜宜用猪油,这样能彰显其香味,当然也能彰显其色感,猪油给所有食材增添了水润,雨露润泽后的花圃内,红牡丹、绿玫瑰、白芙蓉争奇斗艳。
藕心菜是脆嫩的,咬开后,会感到汁水从中漫溢出来,这汁水有一丝微甜,甜而不腻,甜得妥帖。它在一桌的食客面前,是含情脉脉的,只有到了食客嘴里,才能流露出款款深情,它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托付给了舌尖,清香留齿间,让人恍惚中以为来到了月色下的荷塘。
生活处处皆方便,藕心菜也有了方便装,前几日,我在网上买了几袋皖地所产的酸辣藕心菜,这种感觉就像拉着山西婆姨的手在江南一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