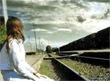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人,后来我们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我认识的这个人他姓徐,在这里我就用徐老师称呼他好了。
之所以将我把徐老师作为忘年交的一个朋友,是因为认识徐老师的那时的我,只有二十岁多一点点,而徐老师已经接近七十岁了。
刚刚认识徐老师时,我并不知道徐老师的过往,只是觉得徐老师那清瘦矍的面相,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人有一定的修养。深陷的眼窝里那一双眼睛,在与人交谈看着对方时,好似有一种穿透力努力地在看着人。
因为徐老师他的这个特点,这让我产生了对徐老师有些好奇的感觉。
对徐老师的由好奇转为想得知他的过往,起始于认识他的第二年。那一年也是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
有一天,街上一个在校的高中生,来到我工作的食品站里,说是找徐老师给他补习英语。我听了之后非常纳闷:这徐老师七十岁的人了,叫他给自己补习英语,难不成徐老师还懂英语?
也就是在那以后不久,我才知道,徐老师不但对英语有较深的掌握,可以辅导高中同学的英语。而且徐老师还订了一份全英语的《中国日报》。我想,这在当时我工作的场镇上乃至于全县的乡镇,包括现在的都是不可多见的事情。
在与徐老师慢慢从熟识到以后的朋友的过程中,我慢慢地得知了徐老师是一九四四年的四川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的县份上,干上了一份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的事情,后来又干上了党部书记。那时的那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其实就是一个秘书长性质的职位。
本来,按照命运的安排,后来的岁月中徐老师也许就成为新中国的罪人,或是在而立之年就被“专政”了去另外一个世界,亦或是在牢狱中度过一些岁月。
可是,天公作美,一个面容姣好且有文化的学校老师年轻女子,在他是党部书记的时候,进入了他的生活和情感世界。
后来在我与徐老师成为朋友后,听徐老师说他与那个女子俩人于一九四五年结了婚,直至一九四九年的六月有了两女一男三个小孩。
徐老师说,就在快要临近一九四九年十月前的八月份的有一天,他自己在到上班去的途中,因为有东西没有带上,而折返回家后的徐老师他,于家里寻找遗忘的东西时,忽然发现在床头下的一处地方,竟然藏着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手枪。
而就在徐老师极其惊愕失色之时,他的那三个孩子的母亲,也就是徐老师的妻子这个时候,也从外面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当看到了那手中拿着自己那支手枪,而呆立在家惊愕失色的丈夫的徐老师他后,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没有一丝的犹豫就夺下了徐老师手中的枪。然后正色对徐老师直言道:“老徐,我本来想再过一段时间就告诉你,但是今天这个事情你知道了,我就提前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我是中共党员,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新中国的诞生就在眼前,你所服务的旧政权已经是日薄西山行将结束了。我希望你认清现实,不要执迷不悟!你可以将我送去监狱,但是,等待你的是什么呢,你今后的下场是什么,我想我不说你也十分清楚!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言毕后转身离开了呆若木鸡的徐老师。
发生这件事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下班回到家里的徐老师,看到了卧室的桌上有一张字条。字条上面写道:
“老徐(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虽然我们年龄也不大,但是一起生活了五年的时间,我看你们老家也就是当地人夫妻之间,不分年龄经常是这样称呼对方的!):自我们俩人经人介绍之后结婚,算起来已经是五年多的时间了。
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你县党部书记妻子的身份掩护下,成功顺利地完成了我的组织交给我的各项任务。为此,我非常的感谢你!
但是,自打前不久你知道了我真实的身份后的那一天起,我知道我与你一起生活的缘分已经走到了最后。虽然我们一起生活了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加上认识接触的那几个月,算起来一共是六年的时光。我也知道和理解你对于我的爱。当然,也知道你在得知我的真实身份后,由爱转生怨恨的心情。
尽管我们从相知相遇,也有了三个儿女。可我们是两个不同信仰的人。你为了你的所谓的三民主义,竭尽所能。我为了我心中向往并为之努力奋斗的共产主义,愿意付出我的一切!因此,在我的心里看来,我们之间之所以能有机会成为夫妻关系,是因为我的工作和信仰需要我这样去付出。
现在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缘分也就结束了。组织上有新的任务等待着我去完成,我当然也就选择了离开你!
我今后的工作不允许我带着三个孩子。所以,三个孩子就留给你了。如果以后条件允许,我会把三个孩子接走,也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不管你是爱我还是恨我,都把我忘记吧,老徐!
你曾经的妻子李,公元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
徐老师说当他看完字条后,一整天不愿意和没有与人说一句话,也没有进一点东西……
不久之后,新政权的建立,徐老师作为一个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虽然没有命案在身,但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仍然是新政权的专政对象,按照惯例应该判刑收监服刑,在监狱里走过他的余生。
就在武装工作队即将对关押的徐老师实施手段,采取相应的措施时。武装工作队接到上级通知,指示和要求武装工作队立刻将关押的徐老师,由判刑收监服刑劳动改造,改为释放回家由地方政府监督劳动改造。
于是,徐老师说他就带着三个小孩回到了老家的村子里,通过自己一个人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
日子到了一九五八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原来由徐老师抚养的三个孩子也越来越大了:大女儿十三岁,二女儿十一岁,小儿子也是十岁了。
由于徐老师一个抚养生活的压力大,三个孩子的身体健康很不好。
就在这关键的档口,有一天两个公社干部突然来到徐老师的家,递给他一封信。
徐老师说他打开信一看,信是由徐老师的他那个曾经的妻子,也就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写的。
信上说为了人三个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今天她委托公社派人来将三个孩子带走,然后四川的组织上会安排人,将三个孩子送到自己工作的北京身边来。
同时,信封里还给徐老师他带来了一百块钱和一百五斤粮票。
也没有等徐老师说什么,两名公社干部说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来接小孩的车还停在公社政府那里等着三个小孩去上车。因此迅既领着孩子离开了徐老师,到公社上车去了。
后来,不久,公社政府又按照县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将徐老师安排到了街上的集体商店,当了一名集体商店里的会计人员。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在造反派组织的强烈要求下,徐老师又回到生产队去劳动改造。直到十年后那场“运动”结束,“拨乱反正”的一九七九年,公社又按照县上的要求,通知徐老师回到街上的集体商店里工作,继续干他曾经干的会计工作。
在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开始到来的“粮食关”而离开了父亲后,跟着自己母亲生活的那三个孩子,也直到了一九七九年的下半年才与徐老师有了联系。大女儿给他写来了一封信。
徐老师说这个时候他知道了自己的三个小孩,大的女大学毕业后,在香港那边工作。二女儿在武汉的一个造船厂工作。小儿子则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泰安市工作。
也是在大女儿的来信中得知,她们的母亲在那场“浩劫”运动以前,就已经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的行政十二级高级干部了。而在那场“浩劫”中靠边站后,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一九七三年又回到原单位工作。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才回到领导岗位上工作。
一九八零年的五月,徐老师说他的大女儿给徐老师他寄过来五百元钱,说是给他的车船费。叫他从成都出发到重庆去坐船到武汉他的二女儿那里,游玩之后再去泰安看小儿子。最后由小儿子办好手续,送他到香港去游玩十天。
收到信的三个月后,徐老师就按照大女儿的设计路线,前前后后游玩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打那以后,每一个月徐老师都会收到大女儿寄给他的三百元外汇券,说是让他去买一些喜欢的又要凭外汇券才能够买到东西!
一九八八年徐老师办了退休手续,被选为县政协委员,继而又到县城里,专门写他在国民党县党部那一段情况的县志情况,也算是人尽其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