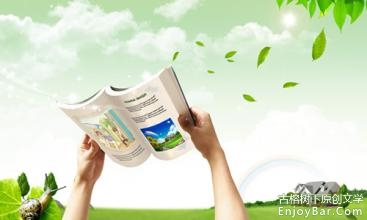西安的这座城市终将是下了雪,虽然不大,但足使人兴奋。穿了保暖的靴子,但并没着厚重的棉服,只将秋日里几件薄衣套在一起。
房间开了落地的小暖灯,照着脚下那一小片地方,有着说不出的温爇。冲一杯浓浓的绿茶,轻靠在桌台边上,听着窗外车水马流的声音,然后将砚台里的墨在宣纸上铺染开来。
墨香,随之满溢。
有时候,很怀念曾经的光景,但究竟还是繁华过后的萧条,也只是在一张纸上留念。
总是以为,自己可以逃离,但终究还是逃离不过。
灰色的天,一直沉闷着,压抑无助。
于是用尽一辈子去寻找来世,却只在梦里谈论今生。
对着佛龛,轻轻诵着经文。
老人们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于是在每个晴朗的夜晚,我都会抬头努力的寻找,但永远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星在哪里?天空依旧是深沉寂寥,霓红闪烁着些许的疲惫。
有本书上面曾写到:命运总是会给那些快乐的人一些意外的收获。可是我总是快乐不起来,所以,我没有得到命运的眷恋。从一开始就没有,以后也没有。
我想起小娜。
小娜曾给我打电话高兴地说西藏真的很漂亮,坐在车上,看着清澈的蓝天、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峦,一切都是那么地飘渺。
我只笑着说:等回来的时候给大家带点好东西。小娜说她想留在西藏,这里会有她的梦。
我说:那就根据你的意思吧,想回来了就回来,不要勉强自己。
小娜说:会的。
我就听到了哭声,听到电话挂断的声音。
我不知道小娜是不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我想一定会找到的,因为她是快乐的,是善良的孩子,她会是上帝的宠儿。
那么,或许有一天自己的那颗星突然发亮,然后很快的消失掉,像梦境一样虚幻。
我喜欢这样的梦境。
三月一个清晨。
六点。
天色微蒙慵懒,让人有种混沌的感觉。没有去穿鞋子,光着脚踩在地板上,任凭冰冷刺痛着脚底,然后传送了整个身体。窗外大岛樱开始盛开,望过去,像是一片云。风吹过,云就落在了地上。
敬晨曾告诉我他最希望的就是做一片云,一片白净的云,自由自在。没有世俗的烦恼,没有世俗的压迫,就这样静静守候着,然后随风飘散。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光线将他将棱角分明的脸庞剪的斑驳,带着一丝疲惫。
一直对娟子说,我不愿意用太过华丽的文字去纪念一个事情,那会是我的痛,越华丽的文字越会让我内心无法释然。平淡,才是最好的,内心只是想要那份宁静而已。
空荡的房间,老式的格纹沙发,将自己蜷缩在里面。
娟子说:你需要一张床。
我说:床是属于两个人的东西,而我并不需要它。
娟子转身,将佛龛前檀香点燃,低着头,用手轻轻抚摸着佛珠。许久,她将头抬起,看着我,又将目光移开在窗外。
她说:花全部开了。
我说:天暖了。
然后我们都保持了沉默。
风起。白色窗帘在风里飞舞着、盘旋扭转,如同满天飞絮。落下来,干净清新。
二十三岁的时候,我对自己说:等将来老去的那一天,我会找一个无人的地方,将自己所有的梦想和画笔都埋葬起来,然后静静躺在床上,然后将整个青春再去做一次梦。
然而有些事,命中注定。
我们必须服从上天给与我们的安排。结局是什么?我们都不曾知道。
佛说:如若欲求,便得苦。如若痴情,便得痛。形形色色,色色形形,天地万物,以色为本,以色为无。放下,便得自在。
我努力过,却还是放不下。
有些东西已在我的生命里扎根,生长。始我茫然、心痛。
梦中拂袖轻叹,一朝揽尽千重。
夜下的西安依旧是寒冷着。匆忙的脚步夹杂了汽笛声,街道边上小贩拢着双手卖力地叫喊,店铺里音乐重复播放那些从没有听过的情歌。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用力地穿透每一个生命的本体,直到碰撞在灰色剥落的城墙上,才软弱下来。角楼铜铃声响,响彻了西安的每个角落。
这座古城便活泛了起来。
而人们,就在这活泛中固执地生存。
夜空上,几点星光。
手中茶已凉。
天气渐暖的时候去了卧龙寺。
这是一个神圣的所在。
青砖瓦砾,古木荫庇。简朴、崇高。每一次抬头仰望,每一次心灵洗礼。
寺庙里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味,喧哗被阻挡在古色大门外。走过青石路,佛号声声,悄悄传递着陀佛的极乐,烦躁的心,霎时警醒。在这个历经千年的寺院,见证了太多的凡俗,终究给了世人一丝净土。
大悲殿,菩萨宝相庄严,善男信女,焚香叩拜。
这里,她能看到各种苦难。这里,她让各种苦难都得到解脱。
一思一浮生,一念一清净。
双手合十,心中诵唱。
时至中午,出了卧龙寺,顺着城墙边的公园,慢慢行走。阳光,开始暖暖地照在身上,泛着惬意。空气里飘荡着杨槐花的余香和护城河水的腥味,让人朦胧,惆怅。
闭上眼睛,站在公园里的古亭中,听那陀螺声。
这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在陀螺快速地转动下,无限拉长,然后幸福着消失。
光阴苒苒,不可饶恕。
我们曾经轻许了那么多誓言,如今早已远走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