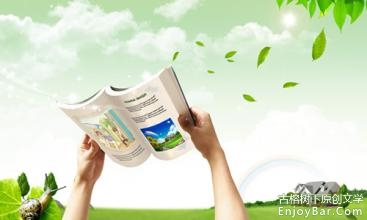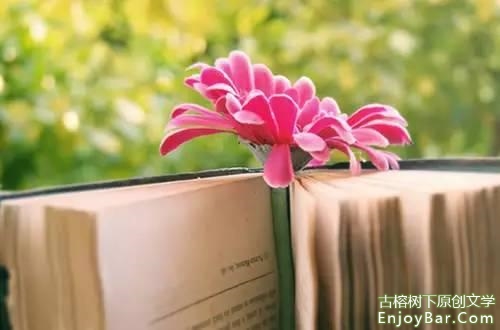贾鲁华
散文家简默新出版了散文集《时间在表盘之外》。初看封皮,烫金的标题下边布满了指向不同时刻的表盘,整齐的三横三纵的表盘与留白,较为精准地契合了散文集的标题。然而,用散文构建时空确为一种冒险,虽然散文的文体特征已然使得散文主题的边界一度拓展,俨然一种包宇环内的气魄,但是散文相对短小的篇幅使其表述的主题宽长度都受到了限制。因此,能否在自己的思考中撑起一个与时间相关的时空架构,对简默而言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恰如简默自己所言:“是时间串起了我的写作。”不管是成长过程中“人间”的“纤尘细埃”,还是人心中自然界诸种“风物”的生存状态,抑或是“远方”神奇的景致和神秘的文明,都在时间中驻足,而又在“表盘之外”活生生地呈现。即是说,成长的经历、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和对远方的寻觅构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丰满“时空”。而这时空的纹理处是简默从日常生活到心理沉思的叙写,是简默对生命体悟持续掘进的冲动、自觉意识与沉思。当然,“时间在表盘之外”的表述是一种文学性表达,简默的述说仍然是在时间序列中进行,只是超越了一种自然性时间观念,对生命的体悟作为时空构建的核心。
一、成长状态下的烟火生命
简默的散文有着显明的叙事性特征,总能在成长经历的“纤尘细埃”中发掘出对生命的思索,可谓微言大义的具体表征。简默将这本散文集的第一部分命名为“人间”,主要叙写了自己成长经历中的种种物事,从儿时“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到父亲去世“催熟”了少不更事的简默,少年的懵懂、青春期的悸动以及中年的生命沉思,皆在一点点夹杂着痛感的回忆中鲜活地呈现出来,在时间的序列中得以重组:“……在时间的标记和界定中,收集起散落一地的记忆碎片,重新拼贴、黏合、打磨、还原过往。我在重塑时间、拒绝遗忘,我的写作也像珠玑。在努力照亮时间深处的暗淡与浅薄。”时间洪流中得以重组的生命历程,在简默的散文中呈现出斑驳繁复的结构,而其中简默“夹杂着痛感”的生命体悟及其清晰的底层视野将其斑驳繁复融为了有机整体,恰如简默坦言:“(父亲的去世)我真实地感到了失怙的苦难,以及根植其上的疼痛,这给我的写作打上了苦难和疼痛的底色,也让我推己及人地唤起共情,将这底色延伸和拓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色人等。”这种夹杂着“苦难和疼痛”的生命思索及底层视野不仅让简默的散文打上了严肃的底色,并且使其视野沉入底层,关注着人世间的芸芸众生。记忆永远是人心中曾经的梦幻,梦幻空间的构建总是建立于作者现时的文化思索。在对“人间”芸芸众生的叙写中,简默的散文展示了儿时的记忆、乡愁、青春、死亡等主题,甚至还有“非正常”生命状态的展示……这过于庞杂的主题被简默归属于一条“成长(记忆)”的线索之中。“人间”系列散文中还有一篇特殊的文章:《K15路车》,这篇散文表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乡土逐渐后退导致的人世无根的生存状态,可以看作是简默当下的文化思索,从而成就了简默力图从儿时到现时对生命思索的宏阔视野。
简默善于将自己的过往细节化地呈现于散文中,而细节的构成却超越于自我的框架推广到了“人间”的芸芸众生,使其散文看起来充满了日常生活化的烟火气息,但同时又展现出简默对人生存状态的深入挖掘。他在《三线流水》《1983年的青春期》中看似记述了个人化的童年故事和青春的萌动,但是推己及人的童年生活中又融入了“三线建设”的个体性表达。在《三张床》《三盏灯》中构设的“床”与“灯”的意象在翻检记忆的过程中又勾连起成长的内在理路。他近乎繁复地叙写着东方机床厂的内部结构及外部环境,探索着“物探队”的秘密与孩童之间的关系。从胜利到刚子、到捉弄胜利的游戏,再到罗平及其女朋友,还有棋牌室下棋的女人和物探队的“表妹”,这些人不经意间在同一时空中相遇了,相遇的那般巧合而又自然。虽然记忆重组了过往的生活,但这似乎是生活的自然性使然,抑或是有意为之?这成就了简默特殊的散文构建模式:发散的、不聚焦的散文构建方式,使得简默的散文看似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似乎只是随意地记载着一些往事,却又自然得无可挑剔,一个人物连接一个人物,一个群体连接一个群体,相互交织成一个个“有趣”但又充满儿童“顽劣”的物事,时时让人忍俊不禁。而“床”和“灯”的意象将成长的记忆具体化、形象化,同时又充满着哲思。简默似乎刻意回避着“三线建设”本应该有的国家叙事,从东方机床厂工人子弟的童年“趣事”中挖掘着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流动,从自己的过往中体悟着“逝去”时光之于生命的构建过程。
生命在持续地流动。《时间在表盘之外》和《溯河洄游的乡愁》就关涉着乡愁和生命的持续流动。乡愁是每一个离家游子的“伤疤”,父亲从贵州走上海回山东,直到最后举家北迁,母亲沿着北迁的路线三年一次地从山东回贵州,被时间丢在表盘外而再不能相遇的晋华从山东回了家乡青海……“他们又像一条条湟鱼,溯着去时的路线,洄游故乡。乡愁如风一路吹打着他们,似浪一路助推着他们,伴着他们回到埋有祖先和自己脐带的地方。他们身后拽着幼小的儿女,让他们熟悉故乡的山河、草木与气息,临走时将这些打进包袱,装入胸中,从此做一个有根的人、浑身结满乡愁的人,晒一缕阳光,淋几滴细雨,都觉得幸福无比。”在中国人心中,“家”是归宿,是无数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所谓“叶落归根”“倦鸟归巢”,它大多时候无关乎外在物质条件的好坏。在简默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吟诵“乡愁”的细节。而对于祖籍是山东却出生在黔南的简默而言,乡愁似乎更复杂一些,儿时在黔南的记忆亦成为简默散文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散文《时间在表盘之外》表面上叙写了因父亲的乡愁而举家从黔南搬迁至鲁南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变化,但时而父亲的乡愁时而母亲的大米、时而黔南时而鲁南、时而个人的寂寞时而守护铁路老头的记忆、时而体育生的荷尔蒙时而女生宿舍被烧破洞的衣服,还有新华书店高个子的女人和被迫承认的早恋……简默用他神奇的笔触书写着新生活的变化和开始萌动的青春荷尔蒙。简默的这种散文写法被学者称为“意识流”。事实上,我更愿意将这种“意识流”的特征理解为简默对原生态生活的认真描摹,原生态生活所具有的偶然性、非逻辑性特征在简默的散文结构中高度呈现、还原,达到了日常生活与散文内容、散文结构同构的文学创作境界,从而使得简默的散文具有着强烈的烟火气息。然而,简默对烟火生活的叙写并非仅仅像“新写实小说”脉络中的“一地鸡毛”,而是于其中体味着日常生活的细节,于生活的日常形态中挖掘出独特的生命体悟:“(暑假开学第一天)到了这一天,这一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年就像一架跷跷板,一头高高撅起的是举步远行拒绝回头的日子,另一头是拔足欲奔日夜兼程的日子,等待着一天天地被招安,新的一架跷跷板又在不紧不慢中拉锯似的开始了新的争夺……”简默在搬迁前后的“纤尘细埃”中体味着生命的存在,挖掘着生命的内涵,当然还有青春的悸动。
《一夜沧桑》叙说了青春的迷惘和消逝。简默在这篇散文中从高考失利写起,写到了自己的初恋,却又鬼使神差地写到了生命的异类形态:傻子与疯子,这是青春迷惘的展现?抑或是简默通过这种近似于“极端性”的叙写体现了其对生命无常的沉思。这种异类生命形态在《篡改》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思考与深化,人生有太多的偶然,某一个细小的错误或挫折都有可能“篡改”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和生命形态。简默带着自己的“痛感”述说着芸芸众生中的异类生命形态,而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傻子或疯子都是那么的年轻,其中关涉的青春迷惘与青春消逝让我们感同身受,青春随着“痛感”消逝了,“结束”了……多么“痛”的生命体悟!
在简默的散文中,生命的逝去是参与其人生思索主题的重要元素之一,但简默总是让死亡与希望同时出现,从而神奇性地在“时间的横断面”上书写着生命的记忆、当下生命的沉思和对未来生命的想象。如前所述,父亲的去世“催熟”了懵懂的简默,让简默的生命与散文底色充满了“痛感”,但是简默并未在“痛感”难以忍受时放弃对“痛”的体悟,而是在对自己过往生活的记忆中“玩味”生命的“痛感”,在日常生活的纹理中寻找希望和温暖。简默将对“希望和温暖”的寻觅放置在了生命的病痛甚或逝去的路径中,形成了一个奇怪而又自然的辩证叙事。在《医院》中用绵密的语言叙写着医院参与构建人生走向的过程,反复述说着父亲的病痛和逝去;在《生命凋零》中写到自己对“痛”的敏感,叙写了各种各样的病痛和死亡:癌症、车祸和流产导致的胎儿死亡……在《医院》中,简默让朋友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婴儿巧合般地躺在了父亲曾经躺过的病床上,生与死的交替在这张病床上呈现,逝去的至亲如同流逝的时间,从此只能在心中寻找记忆的痕迹,但新生的欣喜及其生命走向却呈现出希望的光芒;在《天堂边的孩子》中,简默通过自己的儿子给他的爷爷上坟的过程,于一片肃穆的景象中看到了孩子送葬和孩子上坟等情境,还见到一个提着编织袋捡垃圾的孩子、抢食祭品的孩子……在墓地这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简默静静地缅怀着逝去的亲人,而同时又看到了不同生存样态的孩子。简默在这似乎“奇怪”的思维中完成了一个生命主题的思索,在生生死死的现实世界中完成了生命的无限性延展。
简默用手中的笔串联起诸多人物、诸多人生阶段和诸多精神状态,从青春期的悸动到死亡、从生命的深刻体悟到精神病人的世界……简默就这样犹如坐在“K15路车”上,看着公交车“埋头拼命追赶着时光和速度”,看到了羊群、广告牌、楼房等现代的、前现代的甚或后现代的各种物事,默默地看着乡土和乡村的逐渐消逝,看着城市的不断崛起……这些物事及其思索似乎都在时间的表盘内被结构,抑或是在时间的表盘外悠然自得,但都共同承受着生命的无常,指向深邃生命的纹理。
二、自然“风物”中的视野拓展
在被命名为“风物”的系列散文中,简默将视野从自我的成长经历扩展至自然界,创作了诸多关于动物植物的散文。但很明显,简默并未给我们创设一个静止的动物植物生存空间,而是将其放置于一个动态时间流逝的轨迹之中,用种种异于人生命的鲜活存在串联起了一个个人和一件件事,指向的领域一方面有着简默散文一贯的主题展示,如对儿时无忧无虑生活的记忆、对故乡的怀念等;另一方面亦呈现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察及在此基础上对人性甚或对现代化的反思。在简默的散文中万物有灵。在《河上漂下一群羊》中看到了将被剥下皮囊的羊的潮湿眼睛,从中体味到了羊们掩饰不住的怯弱、安静与善良,进而将自己放置进忧伤的氛围里;在《一辆牛车进城了》中看到了“一声不吭、兜住眼泪”待宰的牛,它们“天真无知”;在《薄如大地》中看到了“瞪大圆溜溜的小眼睛,警惕地睃视着周围”的刺猬,但它终未逃脱城市滚滚车轮的碾压,成为了大地上一张薄薄的皮……翟文铖认为:“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人与动物之间的对抗关系、人类的贪欲和现代化进程制造了数不尽的动物悲剧。”近些年对人欲望的不断生产、人对自然无止境的搜刮,乃至于对现代化的反思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是像简默以这般敏锐的视角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现代化的方式确实少见。在对小动物拟人化的书写中,在直逼动物与人之间关系的逼仄空间中,简默的书写领域及其对细节的展现令充满贪欲的我们触目惊心而又无地自容。
不同于上述几篇散文对城市与现代化的反思那般直接,简默在《蝈蝈纪事》《蜻蜓记》《三脚的猫》《与寓言有关》《家里家外》等散文中,写到野生的、家养的诸种动物,一方面仍然沿袭了对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思索,另一方面却融入了简默熟悉的“记忆”元素,通过蝈蝈、蜻蜓等物象穿越时空,恢复了简默发散的、不聚焦的散文结构特征,时而鲁南时而黔南,时而当下时而几十年前,时而我,时而他,时而儿子,时而外婆……简默用动物勾连了曾经与当下的诸多人和事,重构着自我的生命时空,于其中继续挖掘着我们难以企及的生命深度。
蝈蝈和蜻蜓是自然界中异常弱小的生命存在,简默将其纳入自己的视野中,并非仅仅是因为其弱小而感叹生命易逝,而是将其作为一个中介关联起对人、对事的叙说。蜻蜓勾连起童年的记忆到青年时期的生命存在,关涉到儿时黔南和少年时鲁南两种不同环境的生存样态,亦“串起了我形影相依的孤独时光”。而由于环境的恶化和人对动物植物生存空间的侵占致使蜻蜓越来越少,简默对现代化的反思融入了自我的“记忆”主题中,构建起一个繁复的话语结构。在《蝈蝈纪事》的开头,简默虽然也写到了蝈蝈的逝去和人对弱小生命的禁锢,但简默继而将笔触延展至外婆称蝈蝈为“叫乖子”的事情,由此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过往生命中外婆的形象顺势而来。记忆中,外婆的小菜园和长方形的院子中有着简默儿时的生活种种,被蚊子咬和外婆为简默止痒的细节分明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人关爱子孙的情境。仍是一个夏日,简默回到外婆曾经生活的黔南小城,同二舅祭奠外公和外婆,竟然听到了藏于草丛中的蝈蝈的鸣叫。儿时的记忆又瞬时泛起:作为“玩家”的二舅踏遍一片黄豆地为我捉了一只“绿如翡翠的蝈蝈”,二舅和外婆的关爱陪伴了“一个孩子孤独而冷清的夏夜,唱起歌谣催送他进入梦乡沉睡不醒”。那些夏夜的温暖随着蝈蝈的鸣叫一次次来到简默的眼前。儿子也喜欢蝈蝈,这是否是简默从外婆、二舅那里得到的爱在儿子身上得以绵延?当我们看到公蝈蝈情愿让母蝈蝈吃掉以达到物种的延续时,我们才似乎明白了“叫乖子”与外婆形象的同构关系,才明白了在人世生存中爱的传承与绵延。
简默对猫情有独钟,在不同的散文中都有猫形象的出现。收入散文集的三篇散文《三脚的猫》《与寓言有关》《家里家外》都以猫为主角,叙写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复杂纠葛。其中有人对猫的控制甚或残害,亦有人与猫的和谐相处,还有牛伯凭借猫的形象抒发对逝去妻子的深切怀念之情。“三脚的猫”如何变为一只残疾的猫似乎是一个谜,但是三脚猫在简默生活中的出现却有着另一番意味。残疾的三脚猫在其正常生育能力中孕育的新生命,在儿子的参与下构建了一部爱的“传奇”,同时展示的是儿子对这些新生命的珍爱,只是无意中触犯了猫对子女的爱,两种不同的爱共同构建着自然界中温情的生命存在样态。只是这三脚猫及其子女必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人的生存事态中,却成为了简默心中及笔下的永久记忆。《与寓言有关》叙写“我”救了的猫、令朋友“恐惧”的猫和被爱猫的主人“吃”掉的猫,这种颇有些“拧巴”的主题被简默融入一篇散文之中,在似乎有些难以把握的生命体悟中书写着猫的“灵异”及其饱有“灵性”的生命存在。
人世生存总会有故事,而故事的讲述却是一种蕴含着思想的技术。《家里家外》一反简默惯用的写实手法,于一种寓言式写作中书写了世俗生活。兰姨有着一双能够穿越阳世、看穿阴间的阴阳眼,而这样一位异人却也有着尘世的生活,她养着并深爱着一只通体雪白的猫,当这种超越于尘世的生存让道于尘世中的生活时,就有了尘世中的生死与烟火气。而最终白猫的逝去让兰姨回归到了尘世的生存状态,甚至归于尘世的兰姨变成了三脚猫的走路姿态。这种寓言式的书写在似真似幻中仍然透露出人与动物“拧巴”而“紧张”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牛伯对妻子的怀念中达到了“宽容与和解”。牛伯的妻子患癌去世,牛伯对妻子的怀念通过妻子喜欢的大黄猫和竹子得以寄存,但是大黄猫随着妻子的去世而失踪,成为了牛伯表达情感的特殊通道,或者说,无所寄存的情感更显深沉。虽然牛伯家院子里后来成为“野猫”的聚集地,但它们无法进入牛伯及其妻子和大黄猫的屋里,在牛伯生存的空间和心中只有妻子和大黄猫才可以进入。于是,猫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寄存地,这是人与猫关系的和解,更是人与人生存中情感的升华。或者说,这是简默对于牛伯与其妻子至情至爱的感怀。
《扛一株玉米进城》和《三棵树》表面写的是植物,但是简默对植物的书写同其写动物一样,总是指向对人世生存的感悟。《三棵树》叙写的是简默散文中常见的“故乡”与“乡愁”的主题。树的意象与“根”相关联:“我脑海中蹦出了故乡、童年这些灼烫的字眼。它们起初是抽象的、支离破碎的,但当我摸索着寻到了它们身旁的某一棵树,这棵根深叶茂的树,像一顶密不透风的华盖,帮助此刻迷惘的我,沿着一条明晰的乡间小路,一步一步地走近它们。一切都渐渐地具体了,完整了,明亮了。道路、屋舍、池塘、河流等各就各位,在阳光下闪着干净而单纯的光芒。”带着这种感触寻找故乡,古老的山西大槐树、黔南荔波的大榕树、东方机床厂的银杏树和父亲栽下的泡桐树一一展现在文章中,其中郁结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扛一株玉米进城》以简默惯有的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生活展示了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悖论,一方面人类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生活便利和丰富的物质生产;但另一方面对于原生态物质的需求却又让人对乡土怀有某种敬畏之情。这在城里人喜欢“自卖头”(卖家卖的是自己田地里的种植物)的购物取向中可见一斑。对此,饶翔从美学的角度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诗意的文字所表达的,与其说是怀乡之情,毋宁说是一种美学想象,这其中,寄寓着作者的价值追求——接地气的人类,与泥土相亲,与自然万物同在,在黑土地黄土地之上,在日月星辰之下,挥洒汗水,辛勤耕耘。这样的劳作自有一种内在的诗意与欢乐……”简默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一种质朴的表达,一方面他承认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性,但另一方面他却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写的不完全是它们(动物植物)与人的对立,虽然有时表面看上去它们与人的关系拧巴、紧张,甚至互相伤害,但最终却在现实中实现了宽容与和解。”
被简默命名为“风物”的系列散文既有着生活自然性、偶然性的表达,又有着极强的逻辑性,用风物(动物植物)及其喻征将相关的人与事纳入其中,进而在探索人与自然时间的关系中反思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并在其中寻觅、构建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三、藏地“旅行”中的生命掘进
简默并不满足于在“人间”与“风物”的基点上挖掘生命的意义、探索生命的深度。在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中叙写人世生存及其生命空间的构建后,简默将目光聚焦于“远方”的青藏高原:“我渴望更多更深的了解,像笨拙的土豆沉入土地,以一个汉族人的视角和心灵,亲近和触摸这片高原与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用心用力写出与众不同的她和他们,写出雄浑高原滋养和传承的藏族传统文化,写出藏族同胞内心深处的质朴、坚定和力量,写出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文明各美其美下的美美与共。”简默在藏族文化空间中默默前行,感受、体味着一种异于自我的生命存在形态,于其中沉潜着自我对生命内涵的持续掘进。并且在“远方”的叙写中信息点突然密集起来,与简默之前清晰的语言和叙事特征截然不同。或许,是生命的沉淀太过复杂,抑或是远方的生命体悟用我们的语言无法清晰地诉说,对一种陌生生存方式的思考,成就了一种不同于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叙事方式。因此,不清晰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也恰是这种不清晰一方面增强了简默散文的繁复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简默还在路上默默地探索着、思考着,思考的未完成性显然是简默对探索精神的坚守,凸显了其精神主体的自觉意识。对一个内地汉族人而言,青藏高原上的文化空间不仅是神秘的,更与纯蓝的天空和纯白的云下那片纯净的自然空间相关,而这个时空中的人世生存为简默对生命的持续掘进创造了契机。珠穆朗玛峰作为世界第一高峰,于人而言则与极限相关,它的壮美和神奇总诱惑着人挑战这第一高峰的自然极限和人类的生存极限,这似乎也是一种生命体味和人生感悟的极限。因此,一直在体味烟火生命的简默将目光望向那片神奇的土地似乎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必然。当简默真正站在珠峰前,他心理的反应似乎很难解读,只能用他的文字或可触摸:“面朝着她,我以虔诚的目光,顶礼膜拜。她屏障似的花岗岩山体,真的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从头顶到身上,都落满了皑皑白雪,却与忧愁无关。是漫漫时光在不停地下雪,白了她的头,也葬她的身于雪。而在我眼中,她更是一面晒佛台,顶天立地,圣洁晶莹,无数信众默默地瞻仰她,在心中观想自己的佛祖……”这种震撼性的生命体悟在简默以往的散文书写中很少见到。一种不同于烟火生命中的人生探索在珠峰面前呈现,如果说在“人间”与“风物”系列散文中体现了简默散文的细节之美、日常生活之美,那么此处显明性地体现出简默散文的壮美。
从《一个人的寺庙》开始,简默开始寻找珠峰脚下的人间,在“远方”的人世生存中寻觅人类生存的极限。珠峰以亿万年的自然造化成就了其极限,珠峰脚下的人们也在世界海拔最高的生存空间中沉潜着生命。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随处可见的寺庙、玛尼堆、白塔等,传达出藏族同胞生命体悟的信息:“它们本与往生极乐净土有关,在这样的高度、这样的苦寒之地、这样静谧的旷野,像头顶那条缀满勋章似的星星的银河,超越世俗,擦拭出明亮的精神之光。”他们在挑战人的生存极限的空间中默默地沉淀着心中对生命的虔诚,默默地守候着心中的信仰。据此,简默向我们展示了诸多沉潜生命的藏族同胞。比如二十多年如一日一个人默默守候寺庙的桑杰,他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转经、朝佛、诵经……悄然间,七千多个日夜逝去,桑杰竟然可以受得住空虚、枯燥与寂寞,默默地将自己的生命放置于自然之中。这种沉潜生命的生活方式只有在信仰者身上才可以理解。
此时,我们发现简默竟然将现代化进程中对人欲望的反思在神山脚下得到了回应。神山脚下的简默,不仅向我们展示着神山的壮美、信仰的执着与虔诚,更向我们表达着自我心灵的洗礼与对生命新的体悟:超越于尘世的孤独。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孤独的存在是一种能力,人类很难在现代化进程中扼制自己的欲望,而信仰使得神山脚下的藏族同胞与自然融为一体,苦行中潜心修持,于我们而言确为一种沉思、反思自我生命状态的“他者”。
事实上,这部散文集的三个部分:人间、风物和远方,明显呈现为对生命体悟向深处的层级性挖掘。
小 结
读简默的散文,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已然失去或根本并未形成的对生命的细腻感受与体悟。烟火生命的体悟看似是一种日常生活叙事,但却有着无力感与不确定性的日常生活叙事所没有的硬朗,这种硬朗来源于简默用文字试探性地接通了自我生命与时代的路径。简默有困惑、有痛感,这困惑与痛感绝不仅仅来自于父亲的去世,还有他对时代的不断思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乡村消逝的焦虑,对现代化的不断品味,他的创作呈现出一种较强的思考力,促使他从自我烟火生命的体悟向时代命题的思索进发。但是如何在自我与时代关系的反思中继续对烟火生命的挖掘,就不仅要在生命沉静中超越,更要在构建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中增强现实性的思考能力,这不仅关涉到自身与时代,更关涉到一个烟火生命轨迹中的作家如何让自我的生命体验持续掘进的问题。
“实际上,散文之大,并不在于气象之大,也不在于内容之大,而在于作家本身的立场,在于作家是否有一颗博大丰富的理想者的心灵与情怀。”(韩少功《理想者的姿态与担承——“理想者文丛”出版导言》)简默这个在煤城成长和生活的散文家,必将如其先前的探索,像采煤工一样在黑暗的巷道中默默掘进,头戴矿灯行走在暗黑的煤炭中间,狭窄而漫长的空间被明亮的矿灯刺破。而他,默默地前行,寻找着理想精神主体的自觉,执着于探索精神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