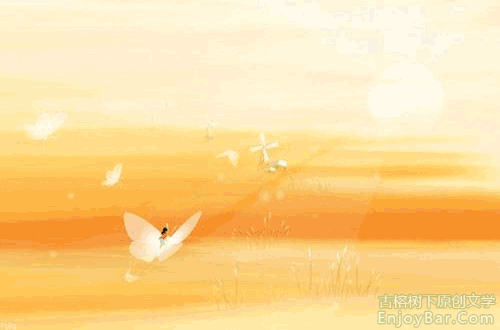三十五
清宁县那天也阴雨绵绵,也是细雨不停,还刮着微风,云层很低,天色很暗,漂浮不定。村上的人都突然感到心神不定,下地吧,路上田间都湿漉漉的,路滑,泥湿。除草拔出一大把泥,挖地泥浆四溅。人们只得留在屋里,修理农具,砍劈柴火,扫扫地,剁草喂个猪这些活计。
陈玉兰突然感觉下腹疼痛,脸色变白,虚汗直流。吴小秀赶紧扶她进屋躺在床上,又赶紧跑回家,还没进屋就大声喊道:“妈,姐快生了!”
吴李氏一听就拉上小运媳妇,跟着女儿一块往学堂跑。进屋揭开被子一看,是要生了。她才吩咐小运媳妇生火烧水,叫女儿找出陈玉兰早已准备的尿布,小孩的衣物和小被盖等,剪刀已经在灯的火苗烧过了。婴儿出生了,是个胖大小子,啼哭的声音格外响亮,仿佛昭告新的生命又降生了,来这个世界了。
“爸,爸,生了。钟武哥的儿子生下来了。”吴小秀跑出房间,高兴地告诉早已侯在外边的人说。
“我都听见了。我兄弟回来,儿子也有了。”吴老汉也高兴地说,他还不知道,就是婴儿降生啼哭的那一刻,钟武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爸,还不知道钟武哥能不能回来。”吴小运担忧地说。
“泄气话,我兄弟命大。小运,那边情况怎么样?”吴老汉问。
“开过庭了,回来的人说,等宣判。”吴小运说:“我又派人去了,这两天就有消息回来。”
“走,回去等消息。小秀,你们照顾好陈老师。”
吴老汉又喜又焦急的带着儿子和两个兄弟离开了学堂。
这婴儿从一生下地就一直在哭,直到哭累了,才歇一会,又哭开了。急得陈玉兰和吴李氏、小秀、小运媳妇束手无策。吴李氏担心是陈玉兰奶水不够,饿着孩子了。而陈玉兰觉得奶水充足,孩子吃的也多。吴小秀认为孩子生下来没见着他爸,哭着想爸爸呢,只有小运媳妇认为是尿布湿了,不舒服才哭。解开换了尿布,还是哭,只有陈玉兰流着眼泪说:
“哭就让他哭,等钟武回来,就不哭了。该回来了,怎么就不见人回来呢?是该到了回来的时候了。”
吴小秀也含着泪,抱着婴儿,不停地在屋里拍打着哄着来回走,累了就和小运媳妇轮换抱。
吴老汉那晚和两个兄弟等得发慌,喝了些酒,各自靠在桌边倒头就睡了。
深夜,门被敲的“咚咚”响,又重又急,吴小运跑去抽开门栓,吴二娃闯进来险些跌倒。
“钟武哥被枪毙了,死了。”说完就哭起来了。
犹如当头一棒,晴天霹雳把大家都惊呆了,吴老汉顿时连话都说不出来,泪水从他眼里流了出来,挂在他那张老脸上。
“二娃,你是不是听错了?”老二吴天云问。
“爸,没有听错。是刘连长告诉我们先回来报个信,好准备办钟武哥的丧事,我们三个腿都跑肿了。”吴二娃说。
“我兄弟人呢?”吴老汉瞪大眼睛,老泪纵横地问。
“刘连长和侯县长亲自送回来。”吴二娃边哭边抓起桌上碗里剩的饭菜就往嘴里刨。
“天啊,怎么会这样?”吴老汉悲愤的说。他气得在屋里来回走,捶胸蹬脚。
“大哥,别急。拿个主意,怎么安葬好。”老三吴天名劝他说。
吴小运蹲在一旁,抱着头说不出话,咬着牙,一脸是愤怒的表情。
吴老汉老泪纵横。前些日子,刘连长还托人捎信回来,说是侯县长请了律师,说钟武罪不至死。他还跑去安慰陈老师,要她养好身子,生下儿子,安心等钟武回来。如今他拿什么话去给陈老师说,这是啥世道呀!人说死就死了,而且还是枪毙。陈老师还说等他回来,念念不忘重办一回喜事,他还答应风光一回,请全村的人都来热闹一回,他怎么向陈老师交待啊。一想到这儿,他抓起桌上的酒灌,扔到地上,摔的粉碎。
“不是说证据不足判不了多重的罪吗?怎么判了要命的罪?”吴天名摇着头说。
“大哥,说说怎么办后事吧?”吴天云问。
“葬在吴家祖坟,既然是我兄弟,就这么办。二娃,他们什么时候送回来?”吴老汉问:“告诉村里人,都去接,全村人都去接我兄弟回家。”
“爸,还用告诉通知吗?你出门去看,深更半夜的都开门了。”吴小运说。
消息传的很快,因为太吃惊了。听到消息的人都爬起了床,你传我,我传你,钟武死的消息很短时间传遍了全村。有的人已经在自家的院坝里烧起了纸钱,一家,两家,渐渐地多了,村里商店的蜡烛、香支、纸钱都卖完了。那十几个被钟武换回来的村民更是痛哭流涕,悔恨莫及,更是在自家院坝里焚香,点燃蜡烛、焚烧纸钱,跪地不起。就连山上居住的人也举着火把,扶老携幼,聚集到了村口桥上桥下守候迎接钟武回村。
教堂的钟敲响了,洪亮的钟声在村子的夜空回荡,沉闷而催人泪下。
“老二,老三,你们马上安排下去,墓坑要挖深,棺材要最好材料制作。不行,还得多刷几遍漆。小运,你告诉各家各户,扎花圈,制丧幡、丧花。”吴老汉吩咐完毕说:“走,我们都去和村里人接我兄弟回来。”
这是梨溪人的一个不眠之夜,村里的空气弥漫着纸钱烧焦的气味和香火的烟味,久久不能散去。哭声此起彼伏,没有间断过。
快到晌午的时候,消息传回来,刘连长和侯县长他们快到了。回家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又纷纷从家里跑向村头。
婴儿不哭了,陈玉兰喂饱了他的奶,等他入睡后,替他盖上被子,下了床,自言自语地说:“真懂事,知道他爹回来了就不哭了,我也该去接他了,这么久才回来,把我也等急了,钟武,我接你来了。”
吴小秀和小运媳妇也跑去了,陈玉兰走出学堂的时候,街道上空无一人,她边走边在喃喃自语,含糊不清地说钟武回来重新娶她了。不再只吃那油腻腻的腊肉了,而是穿了婚纱,牵了她的手,一块去了山上的教堂,接受彼得神父的祝福,教堂的钟声为她敲响。村头人太多了,太嘈杂了,她要走一条近道,没有人,清静的很,只有她去接他的僻静小道。她见到他了,在一汪清澈如镜的水面上站着,向她伸出了手,她快步跑上前,张来双手扑向他,是什么这么冰凉,凉透了她的周身。她好似投入了钟武的怀抱,一块旋转,漂浮着、轻轻地一块静静地走了,走回家去了,去看他俩那不哭的儿子去了。
刘一鸣和侯朝闻骑马还离村口很远的地方,就看见村口的桥头和桥的四周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几百上千人,担架上抬着钟武的尸体,被白布从头到脚盖得严严实实。当他们到桥下跳下马,牵着缰绳往桥上走时,桥上的人都让出了道,桥下一群儿童齐声唱起了李叔同先生作词的歌曲“送别”,领唱的还是那个稍大点的女孩。
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扶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
歌声没有伴奏,幼稚的童声伴随着哭泣声而唱出,如诉如泣,悲凉婉转,令侯朝闻泪花滚滚,他走到那女孩前,蹲下来问她。
“这歌是谁教你们唱的?谢谢你们。”侯朝闻朝那群儿童鞠了一躬。
“陈老师。”那女孩抹着泪说。
“陈老师呢?”侯朝闻站起来四处看,边看边问:“陈玉兰呢?玉兰在哪?”他大声呼喊起来,焦急地要命。
“陈老师在学堂。”吴老汉跑上前说。
“在学堂吗?快走。”侯朝闻招呼刘一鸣说。
他把马的缰绳交给刘一鸣,由他牵着马,跟着吴老汉朝学堂跑去,还没跑几步,小运媳妇和吴小秀就抱着婴儿慌慌张张地挤进人群跑来。
“爸,不好了。陈老师不见了,找不着人了。”小运媳妇抱着婴儿气急败坏地说。
“你们都干嘛呢?人都没看好!”吴老汉一急朝吴小秀就是一巴掌。
吴小秀捂住脸,“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垂下了头说:“我害了钟武哥,又害得找不到姐了,爸,你打死我算了。”
侯朝闻拉住吴老汉说:“快找人!赶快找人!”
“村长,出人命了!”一个女人跑来说。
“出啥人命了?”吴老汉着急地问。
“我看到陈老师了,她朝河边走,嘴里不停地说什么听不清,我跟在后边想拦住她,她就扑进河里去了,一晃眼就不见了。”那女人说:“我只听清了一句话,她说她接到钟先生了,那儿清静。”
“快找呀!沿河找,下边有几个回水沱,找呀!”吴老汉此时像发疯似的大喊大叫起来。
吴小运带着一大帮年轻人朝村外跑,侯朝闻也吩咐刘一鸣派出士兵沿河去搜寻。
侯朝闻从小运媳妇手中抱过婴儿,这孩子不哭,还睁大眼睛看他。他忍住心酸抱着这婴儿,带着抬钟武的担架,朝村公所走去。后边是上千的村民和那群唱着“送别”的儿童。
直到第二天,搜救的人才在下游的第二个回水沱发现和捞出陈玉兰已经泡的浮肿的尸体。
陈南堂夫妇也闻讯朝梨溪赶,钟武受审、判决的消息他已经知道了,虽然悲痛、惋惜,但人已经走了。他们夫妻这次过来,主要是把女儿接回去,不能使她一个人无依无靠继续下去了。他之前也收到过女儿寄回家的信,都是报喜不报忧。说什么梨溪的日子好了,村民能杀猪过年,他们的屋里都挂了许多村民送的腊肉和香肠。村里的好多孩子字已经写的很好了,有的已经学完了二、三年级的课程,村里下代人不会成文盲了。她还在信中说:钟武没那么忙了,常常回家做饭了,做的饭还挺好吃。从来不提发生了什么事,要不是偶然从报上读到清宁县审判的消息,陈南堂还不知道梨溪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
当陈南堂夫妇带着家里的活计坐着滑竿,赶到梨溪的时候,正是准备为钟武夫妻下葬的时候,棺材已经停放到了村公所。村公所的驻军全部按刘一鸣的命令撤防到了南华公司广场外搭建了营房。几十个儿童,穿着破旧的衣服的,穿着草鞋的,赤着足的,一副悲伤的样子,流着泪水唱着“送别”的歌曲,村上的人都三五成群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排队等候轮流进去凭吊。
“老侯啊,你还说是你的好学生,都死了!”陈南堂一进去就泪流不止的侯朝闻骂了一通。
陈南堂的夫人趴在女儿的棺材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辛亏有吴李氏和小运媳妇扶住,才没有晕倒在地。
下葬时,最前面的十几个人持丧幡开路,后边是吴小秀披麻戴孝死抱着婴儿,这婴儿还真的明白事理,不哭也不闹,乖乖地任由吴小秀抱着。抬两口棺木的是十六人并排走在吴小秀后边。棺材后边依然是那儿十个儿童,都在头上和腰上系上了白布条。一路走一路唱着“送别”的歌。刘一鸣的士兵也列队参加了送葬,村里近千人参加。
下葬完毕,吴老汉和村民都要侯朝闻站出来说几句,侯朝闻心里难受,话都不想说。
“校长,说几句嘛,村民们的心意。”刘一鸣说。
“老侯,你讲几句,让他俩死得瞑目。”陈南堂说:“难道这是你我当初革命时要看到的吗?”
“侯县长,你不说几句话,大家都不会散去,心都不甘呀。”吴老汉恳求他说。
侯朝闻这才摸摸他身边周围的儿童的头,走上前去,朝钟武和陈玉兰的墓碑鞠了一躬,又转身过来,朝送葬的人群鞠了一躬,摘下眼镜,抹了模糊的镜片戴上才说。
“谢谢大家,我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俩都是我的学生,年纪轻轻就走了,我痛心,你们大家都痛心。为什么呢?他们做错了什么吗?没有做错什么。他们作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吗?没有。他们赈灾,救济灾民,使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人在梨溪村安顿下来,造梯田、造地、挖煤、造船,挣钱还债,教书,没有一件不是小事,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如果他们不作这些事,只顾自己苟且偷生,也许他们还活着,但是恐怕梨溪村早就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了。他们的这些小事值得我们骄傲。”侯朝闻摘下眼镜,伸手抹湿润了的眼睛,又戴上眼镜说:“辛亥革命几十年了,共和也喊了几十年了,他们还是死了,想起来就是一种悲哀,是这个世界的悲哀。钟武和陈玉兰只是微不足道的人,但他们作的事,值得我们大家尊敬,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中国一两千年,老百姓都没逃脱挨饿的命运,都是饥寒交迫中与命运抗争,钟武、陈玉兰和你们一道抗争了,努力了。现在他们走了,他们是为了你们大伙牺牲了,再也回不来了,请大家记住他们。”
侯朝闻话还没说完,全村人都哭成一片,那十几个钟武换回来的村民,又各自走到坟前,一块跪在那儿,痛苦不已。
看到此情此景,侯朝闻心情澎湃。上千年中国绝大数农民忍饥挨饿,吃不饱饭的问题何时才能不再重现。他没想到,钟武更没想到几十年,上百年后,这种延续了千年的饥饿问题在中国农村消逝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彻底消除了,中国农村各地涌现出了类似钟武这样的无数带头人,钟武不再是孤独者了。
突然,有人看到那坟头上有蝴蝶在飞,于是有人叫了起来,化蝶了,化蝶了!众人望着那飞高飞远的蝴蝶,感觉好神奇啊。听到有人在叫“化蝶了,化蝶了!”侯朝闻还以为听错了,一看,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再看,果然有两只美丽的蝴蝶在坟头上方飞了几圈,然后朝远方飞去了。不仅大家惊呆了,他也惊了,真是神奇了,这钟武和陈玉兰莫非真的化成了蝴蝶,双双朝远方,朝着美好飞去了。
侯朝闻说不下去了,他看见村民们那期盼和无助的目光,他也感到无助和苦恼,便和陈南堂夫妇一道去到学堂去整理陈玉兰和钟武的遗物。进屋,一张木板搭床上铺了层稻草,稻草上那张旧了的草席、蚊帐已经发黄破旧。几块木板钉成的案桌上,除了陈玉兰带过来的的相册里的几张照片,就几乎找不出几件像样的东西。唯独使侯朝闻感兴趣的是陈玉兰那些手抄的课本,字体娟秀,工整,笔画清晰。
“带回去吧,老陈。”侯朝闻说:“留个纪念,睹物思人。”
陈南堂夫妇点头吩咐活计收拾包裹,好带走,而自己的女婿钟武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找到。人死了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往后谁还记得他的模样,孙子长大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如果说清贫如洗,侯朝闻和陈南堂夫妇面对这对夫妻生活过的居室竟然如此简陋而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