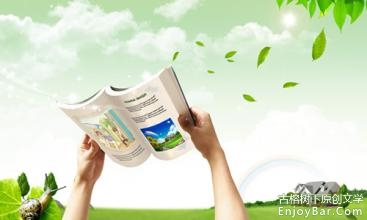城市稻草人(外二章)
稻草人站立在乡村的田野中。不需要房屋。风中雨中阳光中,挺直身板。
在他的想象中,在这八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他也是一个稻草人。孤独,没有伙伴,没有亲戚。没有倾诉的听众。没有房屋(这是最重要的),乡村田野中的稻草人不需要房屋,但是,他需要。但是,他没有。
他是稻草人,又不是稻草人。
城市里的稻草人,没有田野中的稻草人的洒脱与超然。他站立在城市中央,驼着背。
风在背后,雨在背后,阳光在昨天的头顶暴晒。他遮风挡雨的房屋会在哪幢楼房里?会在哪个小区里?
他仰起头,发出无声的诘问,口大如洞,且幽深。
他稻草人般站立在城市中央,风雨中,无法移动脚步。城市耸立的一座座楼房,是一株株玉米、高粱,还是稻谷?
那些馋嘴的鸟儿飞到了哪里?城市,这片田野不需要稻草人,他是城市多余的过客,没有表情,没有房屋的稻草人,在风中瘦下来了,在雨中驼着背。
疼痛的大地
疼痛来自脚趾末端,也来自广阔大地。一棵树,用根须倾听。
众草以花、叶、根、茎,在大雨中熬制汤药。白的露珠、白的骨骼是最后的药引。
一场大雪捂出春的汗珠。春天苏醒。
月亮是一只眼。太阳,是另一只,依旧病着发着烧,烫手。红!
犁铧,割开皮肉,祖父说,大地要来一场外科手术。
大地,空腹服下:红豆、绿豆、玉米、红薯、葵花……大小不等的药丸。村庄瘦弱稀疏的胡须在大地的胃里是放射状的银针,扎疼。
是医治?还是疼痛的一种?祖父以身躯在土地上树立起一个移动的大问号。他的叹息,再一次敲疼村庄和大地的神经。
疼痛来自广阔而荒芜的大地。
疼痛来自强壮而稀疏的庄稼。
比秋天更冰冷的村庄
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晾晒的衣服再次湿透。大汗淋漓的还有比时光更远的思念。门口倒扣的鞋,走了多少路?那些厚而发酵着的泥土又来自谁的故乡?
墙角的向日葵比田野里的都矮,但是颗粒饱满,仿佛不是错过了时光,而是浓缩了四季。
没有了虫子和鸟儿鸣叫的秋天,在雨中收缩起身子。
树们比着最后的绿,用不了多少时光,它们就会比着谁的叶子飞得更远、落得更快。像是村口消失的老人,昨天还说着自己的子女出门走了多久,走了多远,今天,就只有一只矮凳,守候在那里。
等待着,还是守候着。
今天,却只有这些树,还在风中摇晃着脑袋,黑夜里又有多少远归的人,错把树木当成站立或者蹲着的亲人?
只是,它们只是树,或者树桩。风来,凉得很,缩一下脖子,就知道秋天即将到来。
是否,一同到来的还会有浸泡在泪水中的人呢?村庄现在空着,思念与牵挂已经不能将它整个地填满压实。
雨渐渐小了。夜色渐渐来了。
村庄次第亮起的几盏灯有着同样的昏黄,它们的疆域有着几座大山的辽阔,但是它们的光仍然能看得见穿针的孔,针脚起落着,绣着“平安一生”,或者“红红火火”“等你回家”的鞋垫。这些针脚,填满四季所有的空闲时光,却还是稀疏了浅薄了,不能将远行的脚步垫高,再垫高。
如果,远行的脚步走累了,会不会想起一双绣着各色花样的鞋垫呢?“等你回家”,最终,像是渐渐磨断的线头,乱。
那些永远也不可能回来的人,带走了一摞温暖,却真正把凉的时光留了下来,长长地、久久地留了下来。
村庄亦长长久久地留了下来。在凉的夜里,一声咳嗽,让村庄更凉,让秋意更凉。一切都是冰冷的。同时,凉下来、冰冷下来的还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