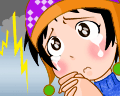程映虹十九世纪俄国革命史上,涅察也夫是一个今人鲜知的名字,至少很多对这段革命史有相当了解的中国人从未听说过他。对于那些希望从正面意义上叙述这段历史的人来说,涅察也夫的棘手之处在于他是一个信念坚定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个极端专制和不择手段的人。因此,...
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由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今年第一期刊发了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希利斯·米勒学术报告的译文,题为《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米勒问道:“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正在给文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
杨宪益四卷本的《新凤霞回忆文丛》即将出版。新凤霞女士是名满中外的戏曲表演艺术大师、散文作家、水墨画家,从六、七岁的幼龄就在京剧舞台上扎了根,七岁起开始学京剧基本功,八岁登台就受到观众的激赏。十四岁改唱评剧一鸣惊人,迅速远近驰名。进入新中国,更以《...
陈国球我的中学教育,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英文中学”中完成的。“英文中学”的英语原作“Anglo-ChineseSchools”,意思是为华人提供英式教育的学校。这比通行的中文名称更能说明问题:相对于“中文中学”而言,“英式华人中学”一直是香...
姜洪读《读书》,需要阅读主体自备“翻译器”,即解释机制,文章发生的背景。我猜一些人之所以说《读书》不好看,恐怕一多半是因为不了解背景: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字。不了解“所指”,也就很难理解“能指”,犹如只给出歇后语的谜面而不给出谜底。这涉及到一个言...
刘纳在一九九六年的中国图书市场,《唐文集》显得朴素、厚重。它昭示着写作的尊严——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人似乎已经久违了的写作的尊严。唐老师始终写得很慢、很艰难。他说过自己写文章是“一句一句地磨,进展甚慢”;他说过有时为了开好一篇文章的头。四、五次,七、...
秦兆基《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三期刊登程光炜先生的文章《诗人李白凤先生》,记叙了李先生的坎坷际遇,读后不禁为之扼腕唏嘘,不过又觉得与自己记忆很有些出入,于是就翻起书来。好在李先生是位不大不小的名人,虽然未见到李先生的长篇传记、年谱,但零星资料一下子就...
在越来越浩瀚的书刊市场上,《读书》实在是很小的:印张,篇幅,价格都微不足道,但是它却一直得到读者和作者们的关心和爱护。不算作者来稿,单是每个月收到的读者来信,就多得无法一一回复,这实在是让我们愧对读者。读者针对《读书》的稿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
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障碍丁宁宁在《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几点意见》(《改革》一九九七年第一期)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大主要障碍是:一,对如何理解、推动“现代企业制度”方面,中央的思想认识不统一;二,改革以来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的固定化;三,由临近的政府...
欧阳军喜近读《读书》一九九七年第十一、十二期安德森的“文明及其内涵”一文,使我想起了“五四”前后的那场东西文化大论战。学术界向来把那次论争概括为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对立。这完全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解。只要我们细究当时论战双方的言论,我...